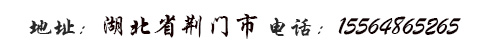谢培军血色石榴花
|
血色石榴花 谢培军 五月,石榴开花了,红得如血。 父亲很喜欢石榴花,开春后就盼望着石榴开花。石榴花开时,天气才真正算是暖和了,赶着水牛下田,脚不再寒冷。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爸爸开始养水牛耕田,靠给村民耕田挣得一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供养五个孩子。 爸爸身材矮小瘦弱,没有其他手艺,干不了什么大事,甚至饭菜也烧不熟。但他养牛耕田的活儿,在村里,有口皆碑,堪称一绝。父亲辈分大,白胡子的老人也敬称他为“才叔”。因耕田的技术精湛,村民都竖起大拇指夸耀说:“才叔的田犁得最好,秧苗一下田,保准就返青,方圆十里无人可比!” 每每得到人们的褒奖,父亲总是憨憨地露出微笑,黝黑的脸庞上牙齿显得很白,他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火,静静地蹲在地上,在人们的称赞声中悠闲的吸着香烟。 其实,耕地犁田这活,有十几年的耕田经验的父亲心里最明白。 要耕好田,就一个诀窍:趁早。 每年稻子刚上粮仓,村民就和父亲约好来年的耕田事宜。一般都是往年的老客户,除非是特殊情况,父亲是不会轻易开口同意的。因为,父亲耕田细致,一天定量耕作,每年就接受几十亩的田地,一年就只能干那么多活儿。答应的活儿,就会精耕细作,按时完成,从未耽误一家秧苗栽期。 父亲与一般耕田夫不一样。来年的耕田农事,父亲在当年霜降就开始了。在秋冬的暖阳下,父亲赶着水牛,驮着犁,把水田翻耕一遍。人们不解其中道理。父亲清楚这冬耕的妙处,这样把稻田泥土翻耕之后,寒冬腊月,泥土里的病虫会冻死,同时,板结的泥土经过霜雪冰冻的作用,来年变得更加的疏松肥沃。 立春过后,父亲就开始整修耕田犁具。热闹的正月刚过几天,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当第一声春雷响彻大地,父亲就早早扛着犁具,赶着水牛,打着赤脚开始了春耕。 惊蛰刚过,太阳暖和起来了,但田野寒冰初解,光着脚踩在水田里,那感觉只有父亲知道,他说:“这冬雪化的春水很咬脚,半天才能适应过来。我就盼着石榴开花,那时候水温合适,不再寒冷。”在去年冬耕的基础上,再次把所有田地翻耕一遍。耕过之后,灌满水,让新翻耕的泥土浸泡在春水里。 这是耕田最艰苦的时候。由于双脚浸泡在泥水里时间过长,双脚常被冻麻木,再加上寒风一吹,两只脚从脚跟到膝盖会裂开道道血口,脚板冻得发白没有血色,一双小腿上的毫毛几乎完全脱落。 记得有一次,父亲在黄昏中扛着犁回家。我早早为父亲准备了一大盆热水,好让父亲泡泡脚,暖暖身子。父亲脱去沾满泥水的衣服,坐在小方凳上,双脚一伸进热水里,眉头紧皱,三四秒钟后,双脚迅速地从热水里缩回来,开大口骂道:“死小鬼,想烫死我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如此盛怒,热水撒了一地。我委屈地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父亲的脸。母亲看着父亲有些浮肿的双脚,含着眼泪说:“别吓着孩子,孩子也是好心,让你暖和暖和,你再把脚放进水里试试,慢慢适应就不烫啦!那酱油汤已经烧好了,洗好就吃吧!” 记忆中,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发火。母亲专为父亲烧的那酱油汤也一直是我想吃到的佳肴。其实,那时家里贫穷,又需要积钱做房子,父亲辛苦耕作。母亲担忧父亲缺少营养,就是在锅里把水煮开了,放入一点盐和猪油,倒几滴酱油,用几根葱花作色,很像现在有些小食品摊上的老板为吃炒面的顾客额外送的油水汤。这就是给父亲特殊的待遇了。我们小孩子是吃不上的,闻着那浓浓的酱油香味,我竟然猜想那一定是世上的珍品。后来住上新房,生活有所改善,才品尝到那酱油汤味道,也品尝到父亲发火的苦衷。 春分时,石榴树梢还刚刚钻出一点瘦瘦的叶尖,布谷鸟在春风里“布谷布谷”叫个不休。父亲已早把所有的田地又翻耕了一遍了。然后,背着平整泥土的田踏工具,在浑浊的水田里,驱赶着水牛,平整水田。 这种工具,父亲常常称之为田踏。它是用杉木制作而成的一个长方形框架,极像“目”字。两侧的横板一米多长,十几厘米宽,横板上各安插着十把锋利如匕首一般的割泥刀。踏板一侧按有一条铁链,便于站在田踏上控制平衡。平整泥土时,父亲把田踏用铁链固定在牛脖子上,赤脚站在两侧的横木板上,左手牵着牛绳和田踏的铁链,控制方向和身体平衡,右手扬着驱赶水牛的鞭子。父亲就像一位驰骋疆场的将军,挥舞着手中的鞭子,水牛奋力前行,脚下的田踏在浑浊的泥水里破浪前进,发出阵阵哗哗的水声。 虽然,平整水田这项耕作,很长时间是被水牛拖着田踏奔跑,人不需走动,但也不是省力的活儿。 父亲身体瘦小,水牛拉着田踏跑得太快,割泥刀插得不深,泥土不易割碎,水土就不易均匀。于是,在田踏的横木上加上一块三十来斤的石头,从而加重田踏的压力,这样淤泥就容易割碎均匀。长时间站在田踏上,手脚常常麻木抽搐,有时没控制好平衡就会在田踏上摔下来,重重地栽在泥水里。有一次,父亲从田踏上摔下来,虽然没有栽在泥水里,可是由于失去平衡,双脚从田踏上滑落下来,水牛拉着的田踏还在飞快向前运动,田踏上的锋利的割泥刀在父亲的右脚小腿上划过,像石榴花一样鲜红的血从小腿肚的一道口子里流了出来,染红了泥土和踏板…… 父亲在河水里清洗了一下伤口,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扎紧伤口,然后踏上田踏的横木,把手中的鞭子一扬,继续平整水田。 父亲知道,如果停下来,就完成不了今天的田地,那么明天村民就会焦急的等待插秧。而秧苗能否顺利成活转青,这道程序是关键。所以,父亲不敢丝毫马虎,否则一辈子的声誉毁于一旦! 当一块田平整好后,父亲让水牛在田边啃吃着从土里刚刚冒出的嫩草,自己坐在田埂上,点上一支烟,看看水田是否平整。父亲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里泥土没有碾碎,哪里没有平整。一般是一次完成,不需翻工的。但有时是山沟里的水田,泥土厚度不一,常常是要加工几次才能平整均匀的。 如此平整几十亩水田,需大半个月时间,水田平整后,浸满水,等到插秧的时候,再做最后一道程序——打浑水。 这个时候,石榴树绿了,血色的石榴花红了,田里的水渐渐温暖起来,可是天气也就炎热起来了。 整平了的水田,浸水后,松软的泥浆会沉淀下来,水也清了。打浑水时,就和平整水田一样,用田踏再重新平整一遍即可,使水田的泥水混合一块,浑浊不清,这样就可以抛撒秧苗,分苗插秧了。当水田的水再次沉淀下来时,淤泥就会覆盖住秧苗的根部,利于秧苗生根,转青,发苗。 这时候,父亲的耕作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插秧的村民往往会毫不吝啬地给予父亲许多赞词,这也是父亲最幸福、最轻松的时刻。 有一回,当父亲打好浑水,一上岸,主人就邀请父亲坐到一棵开满血红色石榴花的树下休息,吃糕点。由于口渴,父亲拿起主人的一只军用的绿色茶壶仰头就喝,咕咚一口下去才知道是白酒。滴酒不沾的父亲反应过来是酒时,已为时晚矣。白酒灌倒胃里,那股热力已浸透到每一根血管,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父亲倒身便睡在了石榴树下,整整睡了一个下午,鲜红的石榴花落在他涨红的脸上,落在他沾满泥浆的衣服上。 当血红色的夕阳照在他脸庞上,他朦朦胧胧醒来,张开血红的双眼,看到石榴树上鲜红的花儿开得如火焰一样好看,于是折了一支,赶着水牛回家,把石榴花扦插在屋旁的路边。 没想到,这石榴树就活了,两三年就窜到人头这么高了,并且在枝头碎小的绿叶丛里探出了几朵红色的花骨朵,像红色的小灯泡。通过父亲的介绍,我第一次认识了石榴花,特别喜欢它那火一般的颜色! 我在县城上中学时,也是在一个石榴花开的季节里。有同学突然告诉我,说我父亲来学校找我。我思忖父亲从来不来学校的啊。我匆忙跑出教室,在校园的一棵开满血红的石榴树下,看到父亲坐在树根上,正等着我。 我停下脚步,站在远处细瞧。 父亲缩着瘦小的身子,左手捂着腹部,右手夹着一支烟,身前放着一把崭新的耕犁。我犹豫不决,这就是我的父亲吗?我好意思在同学的面前认这位乡下农民父亲吗? 但是,我最终还是走向父亲,开口就埋怨地说:“你来干什么!” 原来,父亲耕犁坏了,专门来城里买一把新的,顺便来学校看看我。父亲离开时,从沾满泥水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五元褶皱成不成样的纸币,塞到我手上,说:“快中考了,买点菜,补充一下营养!”当我回过神来,口里轻声喊着爸爸时,父亲已经背起耕犁,背影消失在校园门口了。我站在石榴树下,已是泪流满面…… 那年的九月,在石榴挂果的时候,我考取了徽州师范中专学校。临行前的晚上,父亲如释重负,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父亲又一次喝多了,脸颊涨红得像刚刚盛开的石榴花。 父亲说:“你毕业后,拿工资了,我就可以不用耕田啦!” 几度石榴花开。我师范毕业了,弟弟妹妹还在读书。父亲又说:“我身板子还行,村民信任我,我再干几年!” 我成家的那年,父亲不小心从田踏上摔下来,狠狠的一头栽在浑浊的水田里,好不容易才从泥水里爬起来。我和妈妈才强迫父亲放弃他干了二十几年的耕田手艺。但命运不济的是父亲歇下手中的耕犁,没享受几年的退休生活,就得中风病倒,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也是石榴开花的日子,永远离开了我们! 三年前,我在街道旁花农的手上买了一盆石榴树,瘦小的枝条上,碎小的绿叶丛里探出几朵鲜红的石榴花,煞是可爱。我把这盆石榴花抱回小区,放在家里的阳台上。按照花农嘱咐,一周浇一次水,一年施一次肥,过冬前只要浇透一次水就可以越冬。 每年的五月,阳台上的那盆石榴花就探出了许多鲜红的花蕾,那绽放的花瓣红得如血…… 谢培军,年生于安徽祁门南乡,农村初中语文教师。安徽省散文作家协会会员,黄山市作家协会会员。热爱生活,鍖椾含涓鐧界櫆椋庡尰闄?鍖椾含甯傛不鐤楃櫧鐧滈鐨勬渶濂藉尰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cs/170.html
- 上一篇文章: 吃了这么多年的石榴,竟然现在才发现
- 下一篇文章: 石榴起源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