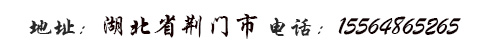野桃花外三则曲令敏
|
北京看白癜风医院在哪里 https://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野桃花 春三月,也不知谁打个响指,点中了桐河的柳腰,这条绕村而过的小河左一扭右一扭,甩出几湾清凌凌的笑涡儿,绿里透蓝,吸进鼻孔淡淡的甜,洇到心里会留下终生洗不掉的斑痕,有点像婴儿小衣衫上的奶渍,但不黄不白也不强,只一味淡淡地紫蓝,悠悠地清香…… 每当这时节,南河边的桃花就开了。天上的云,河里的水,野地里的麦苗儿,刮过麦苗儿的风,一时间和这薄雾似的桃花成一景,引逗得剜菜的女孩儿手搭眼罩儿四下看,天也远,地也远,紫苍苍村树相连,看得她身上发虚发软。风溜溜翻动桃红柳绿的春光,一层层翻开她如花的心事:远远近近的村镇,指不定哪一个是她将来的归宿呢!淡淡的忧苦涌上心头儿,还没有品尝到连根拔下移往别家庭院的伤痛,她就从心里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 不知从哪朝哪代起,人们就开始拿桃花比女儿:红颜薄命如桃花,这还是好的。如果说谁家犯了“桃花水”,那家的女儿不等凋零就成了众人脚下的泥!桃花所以不敢香,就是这个缘故吧?也有大雪压断桃花枝子的事儿,可自古结果子的桃树都散落在郊野,当然比不得深宅大院里的红梅腊梅,除了陶渊明,很少有高人雅士为它哼几句专心专情的诗文来。可人们不知道,这些开在乡野的桃花,会被桃花一样的女孩儿移栽到心里去,比任何诗文都活得滋润,活得长久。 春天,去地里剜草或是拾柴,谁要是碰见一棵四指多高的桃树苗儿,就会扔下箩头,宝贝一样把它起下来,捧回家栽在向阳的墙根儿下,用槐刺枝子栅严实,一天不看看三遍儿。有时候能活成,有时候没等到开花儿,就被猪拱了,羊啃了,再不就是大人们垛柴草、垒鸡窝把地儿给占了。若是真能活到开花儿,求大人嫁接上“五月先儿”、“六月白”,长成一棵树,活个十年八载,那就成了这孩子生命中最幸运的事儿,无论啥时候回想起来,都会心头一亮。 春天又来了,桐河水清澈依旧,那些桃花即使不开在原来的地方,也会开在另外一些不为我所知的地方吧?只是家乡的女孩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还有谁会有闲工夫看着这些野外的桃花儿发一回呆呢? 柳树“清明晒干柳,窝窝砸死狗。” 这句农谚肯定是从一个与自然没有半点阻隔的心灵里长出来的。“清明”,不只是节令,它是被小南风催赶着的大片蜃气,马群一样穿过天边的地平线“啪!啪!啪!”一路拍掉树木们收肩缩背的拘谨,廓清捂了一冬的凋败和浊气,枝条松散开来,把清气全数释放,溶进哗哗撒欢的阳光里,就这样倾天泼墨,才写意了这个涌流于天地之间的“清明”。 我心灵里的三棵柳树离家门不远,就长在南大坑的西北角,是三个挨肩儿的姊妹。她们横枝向天,一看就不是长袖善舞的垂杨柳,与灞桥边系马留人的婀娜美娘攀不上亲,她们天生是折技成林的民间凡胎,无论怎样刀劈斧斫,轻易都不会死。砍下一枝做成幡杆,插在坟上与死人为伴,得点雨水照样发芽儿。那个说出“残花败柳”的人,即便不是个狗屁不通的“薛老大”,也是一段不解风情的呆木头。柳,落地生,见风长,是天地间任什么恶物都驱不散的清灵之气,怎么会败呢? 打从记事儿起,三姊妹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春日,我吃她们的柳絮菜;夏天,我喝她们的柳叶茶。嗓子痛了,哪儿长疖子了,抻手到水里采一把褐红的须根儿,熬水喝。每年春上柳树发芽儿,掰几枝儿直溜的拧喇叭儿,粗的音粗,细的音细,长的悠扬,短的清脆,你吹我也吹,声音被风荡起来,过节一样快活。要是折一枝子细条蓬松的,垫一疙瘩套被子撕下来的旧棉套,掐住根儿哧哩往上一捋,青皮和嫩叶捋到枝尖儿上,就是“老鸹窝儿”。七八个“老鸹窝儿”,坠着白亮亮弹跳的柳枝儿,走一步摇三摇,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乱点头儿”。粗点儿的柳枝,青皮下有一层白白的二层皮儿,舌头舔舔,黏黏的,有点涩,牙硌硌,咔嚓儿咔嚓儿响,响过之后,春天的味道就丝丝缕缕挂在牙缝里了。 “清明晒干柳,窝窝砸死狗。”在大人眼里,清明这天风和日丽,是高粱穗子压塌地皮的好兆头。年事渐长,我不再吹喇叭儿、玩“老鸹窝儿”,针芒一样刺在心上的,是柳枝子上干爽明亮的春光,是柳树投在水中的曲曲弯弯的影子。那是个晴和的清明节,我坐在柳树下的洗衣石上,记不得是刚刚放学,还是刚刚洗完衣服。东南风一阵一阵刮过柳树,刮过树下的我,一开始有两只燕子一趟一趟衔泥,看着看着,洗衣石犁动水波移动起来,柳树的影子也跟着移动,水波上的阳光闪动碎银,斑斑点点被水纹溅起,抛上鬓角儿,抛上眉头儿,撒得一身都是,丁丁当当的光芒渗进胸间,把那颗心弄得钻石一样透亮…… 槐花一间坐西朝东的灶火,四堵土墙抬起山形的麦秸屋顶,背靠着两棵洋槐树一棵榆树,如同一朵瘦弱的草菇。在一个清风不住扇起麦浪的春日,洋槐花开了,一树绿把儿的,雪白里带点儿青丝,一树红把儿的,雪白里带点红晕。成嘟噜成串儿,噙着露水的小嘴儿,抿一口儿清甜,温柔而沉静。 奶奶找出一根长竹竿,绑个铁钩儿,叫我去够些绿把儿的槐花。褐色带刺的槐枝很脆,搭上钩儿一拽,“咔嚓”就断了。槐树不怕折,技越折越旺,叶捋了还生。知道它这脾性,也不去心疼它,咔嚓咔嚓,不大会儿,带花的枝子就落了一地。捡捡堆在灶火门口儿,端个筛子开始捋。拿起一枝儿,从下往上,不光捋花,带些嫩叶蒸出来松爽不腻牙。捋满两筛子,放水里淘淘,淋到半干,拌上面,搁锅箅儿上,扣着锅盖蒸,蒸熟了蘸蒜汁儿,绿把儿槐花比红把儿的好吃。但不知为什么,槐花闻着清香沁人,吃起来甜腻腻的,远没有榆钱和构棒槌儿爽口。正因为如此,只是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人们才会大量采摘,吃不了晒干存起来。大多时候,也就是在花儿半开时蒸上一顿两顿尝尝鲜罢了。 大人们也许不知道,也许早先知道后来又忘了,洋槐花生吃也是不错的。 放学路上,几个孩子一挤眼儿,从路队里拉下来,拐弯儿折进那条大沟,路队长只看见几个黑乎乎的头尖儿,也认不出谁是谁。顺着大沟往东不远,就是个二里多长的水坝,坝子上密密麻麻种着大片的洋槐树。书包朝地下一撂,呸呸往手心里吐点唾沫,找准一棵,哧溜哧溜爬上去,坐在树柯杈上,风摇着那树一晃一晃的,天蓝云白花香,一眼看多远。捋一串儿槐花在手心里,凉浸浸,毛茸茸,像鸟雀儿湿润的舌头,舔得人心里说不出的舒坦。拽掉花瓣儿,拔下中间那根细长的芯儿,搁嘴里一咬,清、涩、甜,口水滋滋往外冒。槐树叶又薄又软,阳光一晒就透,风刮过来沙沙响,细碎又柔和,落进心里,青蒙蒙的,那一刻,人真像是掉进了仙界…… “大槐树,槐树槐, 槐树底下搭戏台。 人家的闺女都来了, 俺家的闺女咋没来?” 谁能告诉我,当年那个生吃槐花儿的女孩儿,如今到哪儿去了呢? 石榴花那是一个曾经千年不变的夏日,端阳节过后,场光地净,麦罢了。中午歇晌的时候,男人们披着日渐稠密的树阴站方、下棋、打扑克,女人们偷空儿缝缝补补做针线。 我坐在槐树底下纳袜底儿,汗湿的针越拔越涩,树上几只蝉吱啦吱啦不住声地叫,还没纳完一根线,就被它们叫得眼皮儿直打架。苦楚一针扎在指尖上,痛得一哆嗦,一珠儿血洇进针脚眼儿,染红豌豆大一块儿。眼看心心念念漂白的袜底布被弄脏了,气得我日楞一声连针带袜底儿甩了出去,不偏不正掉在下坡那棵石榴树上。 坐在旁边纳鞋底儿的母亲看了我一眼,又看看那丛开满橙红色花朵的石榴,为了惊走我的瞌睡,故意破个谜让我猜:“雨落平沙地,新鞋蹅湿泥,豆包去了馅儿,石榴翻卷皮。”我说谁不知道那是麻子的脸。母亲又说:“麻子麻,上树爬。狗来咬,吓得麻子牙龇喇。”我说:“不对!不对!不是‘牙龇喇’,是‘龇喇牙’!”说说笑笑,瞌睡真的被赶跑了,自己扔的袜底儿还得自己去拣回来。 够袜底儿的时候,我摸着树枝儿发软,就知道石榴树渴了,放下袜底儿到坑里打半桶水,贴着树根浇下去,也没听见吱儿吱儿响,靠下边的几蓬树枝子就亮旺旺的有了精神,每片小叶子的尖顶上,都挑起个米儿大的水珠儿。一股花香甜甜细细拂过面颊,直透心底,忍不住伸手摸摸枝头的花朵儿,薄溜溜,肉嫩嫩,噙着阳光随风颤动。那感觉沾在手上,多年后回味起来,还让我想起花季小女儿又白又软的手指,想起少女那方水意蒙蒙的心田,绿柳如烟,桃花明亮,却没有人影,也不见楼台。 后来,在李贺的诗中看到这样的句子:“石榴花发满溪津,溪女洗花染白云。”一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榴花人面两相映的中午。那天我听母亲说,没有黑靛蓝靛的时候,人们就用石榴皮染鞋面,两个石榴能染三四尺布。剥下石榴皮,熬成黑水,端到水坑边儿,揉一遍儿,抹一层臭青泥,捂一会儿,搁水里涮涮,再揉第二遍儿。反反复复揉它十来遍儿,色气就上足了,晒干黑亮黑亮,下撑子扎花绣朵,鲜净得耀眼。 李贺诗中写的,是小女儿流荡天地间的那股洇染人心的色与香,母亲说的才是沧桑女人的生活真相。 曲令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gs/10998.html
- 上一篇文章: 蔡杰显微镜下的匠人
- 下一篇文章: 青春之歌一张票,一首诗,毕业晚会第二轮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