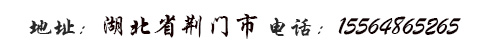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9
|
《石榴花开》原名《故道》,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年定点深入生活签约项目。根据《石榴花开》第一章改编的中篇小说《石榴》,获喜迎党的十九大征文优秀奖;根据《石榴花开》第二章改编的中篇小说《大麦小麦》,刊发于《湖南文学》年7期主编推荐头题,获大美菏泽征文小说故事类一等奖,获齐鲁文学年作品年展优秀奖。长篇小说《石榴花开》年拟出版。 第一章石榴 9.姥爷娶了小老婆 牛运仓被抓壮丁半年之后辗转到了南京,一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自不必说,逃跑的途中曾经一天三次被抓,还曾经一夜三次投降。仗打得乱,一会被国民党抓,一会被八路军抓,一会投降八路军,一会投降国民党,牛运仓最终还是落到国民党手上。说来可笑也可悲,好多和牛运仓一样被抓了壮丁的,被抓来抓去,晕头转向,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哪路兵,跟谁打的仗。 当年,和我姥爷牛运仓一起被抓壮丁的还有鲜花的爹白板凳,我该叫做爷爷的一个人。鲜花,后来成为我爹的这个人,他和我娘大麦我姨小麦的感情纠葛,是第二章的故事。牛运仓被抓时我大舅一岁多,二舅刚出生两天整。那时候,大麦小麦都还是未知数,鲜花还在他娘肚子里,他爹被抓当天夜里他从他娘肚子里钻出来,可是,晚了一步,就差这几个时辰,鲜花和他爹白板凳错过了一辈子。两人在徐州开往南京的途中被分到一个运输队,两人合用一辆小土车运粮食,一个推,一个拉。途中,两人几次合计着逃跑,都没得逞。 一次差点就得逞了。那天下午,下着大雨,两人被一个大个子兵领着去沿途村里拉征牛,跑了大半个村,终于找着了一头牛。两人都成了落汤鸡,牛也成了水牛,任怎么拉,怎么拽,牛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蹄子像长在地上不肯挪动一步,牛主人好话说尽,塞一把响当当的现大洋在大个子兵口袋里,大个子欢天喜地地收了,放了征牛。天已擦黑,陌生的村巷子里空无一人,两手空空的牛运仓给白板凳递个眼色,俩人撒开脚丫子大跑。大个子兵哇哇乱叫一阵,看追赶无望,怀揣着现大洋喜滋滋掉头走了。也合该牛运仓和白板凳倒霉,俩人跑半夜,喘息未定,没来得及欢庆,迎头又碰上抓差的。俩人被打了一顿,又稀里糊涂被抓进队伍。 一天后他俩又遇着那个大个子兵,不知道是他们压根就没跑出同一支队伍,还是大个子兵也易了主,之后不久他俩在行军途中的僻静处,亲眼目睹了大个子兵被身后的同伙一枪托子砸在脑袋上,身上的大洋被抢劫一空。那个同伙骂骂咧咧的,娘的,早分给老子一半,也留你一条狗命。五天后的一次战斗中,牛运仓和白板凳用一根扁担抬子弹,白板凳在前,牛运仓在后,一梭子弹从侧面飞过来,从白板凳的一只耳朵钻进去,另一只耳朵钻出来。牛运仓眼睁睁地看着白板凳摇晃几下,扑通倒地,一梭子血射出一丈远。他吓得屎尿流了一裤子。 一九四三年秋天,牛运仓所在部队北上开往济宁,途经老家,他在一个漆黑夜晚离队换了老百姓服装潜回家。牛运仓回来时带来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是他战友的妹子,战友在一次日军偷袭中为保护他牺牲了。兄妹俩爹娘早在战友参军前就死了,死于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的大瘟疫。 牛运仓是在他回来半年后的一个晚上说出他战友遗愿的。他拿自己的大炮在石榴身上狂轰滥炸之后,有点羞涩有点难为情地说,小姑娘,他战友的遗愿是要他收房做小老婆。石榴折起身把他从身上掀下来,踹到床底下。 那时候,他老婆石榴已经怀有四个多月的身孕。 说起来,小姑娘是个不错的小姑娘,小姑娘名叫青杏。长得眉清目秀,穷人家的孩子,懂事,吃苦,耐劳,手脚也利索,跟在石榴身后,叫姐叫得也甜。石榴喜欢这个妹子,可是再喜欢也不希望她给自己男人做小老婆,心再宽的女人也不会。 石榴又哭又闹,摔东砸西,我大舅二舅成了出气筒,还在石榴肚子里徘徊的胎儿,后来成为我娘的大麦,也受到株连。大舅二舅四五天没吃上一口热乎饭,她自己也四五天不吃不喝,害得刚刚发育成型,像小老鼠一样大小的大麦差点胎死腹中。牛运仓,那个平时看上去温顺的男人,这回像天下所有馋嘴男人一样铁了心,他对石榴的抗争装聋作哑,对石榴的痛苦视而不见。 她婆奶奶说,人犟不过命,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该来的,早晚都会来,她婆奶奶又说,遗愿不可违,给他收了吧。石榴为此也恼着她。 石榴有两个月不叫男人上她的床。 石榴回了水门镇,回了生她养她的地方。石榴坐在马车上哭了一路。 家已不是家的样子,残墙断壁,一片瓦砾,一片凄凉。 那是石榴离家后第一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石榴打问村上活下来的老人,询问她娘她哥的消息。哪里就有消息呢。能活着的,都有音信了,没音信的,多半凶多吉少。石榴不知道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她的小哥正躲在一个壕沟里和八路军激战。她小哥活着,和她也是生死两茫茫,石榴到死也没见着她这位小哥的面。他小哥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了伤,成了八路军的俘虏,也因为这个俘虏身份,死于文革中的大批斗。想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娘和哥,抚摸着腹中的胎儿,想着自己命的苦,石榴哭得悲悲戚戚。石榴在老屋前烧了纸钱,到老再没回去过。 青杏被纳二房是一九四五年夏天。婚事是石榴一手操办的。不算大排场,可场面也很说得过去了,弄了一班响器唢呐,呜呜哇哇吹打了一天。 那时候,牛运仓已被选为朱家寨的区长,牛家米粮行重新开张。石榴所有的委屈,女人所有的委屈,在生计面前,渺小卑微得如一粒尘埃,如沟壑旁的野草。 10、神秘的子宫,丰满的乳房 石榴在她男人回来之后的两年里,又生了两个,一个丫头,一个小子,丫头取名大麦,后来成了我娘。石榴那块田地,有种就生根发芽,丝毫不受外面枪林弹雨的影响,也丝毫不受季节更替天气旱涝的影响,像一只惯于下蛋的老母鸡,嘎嘎嘎,下一只蛋,嘎嘎嘎,又下一只蛋,偶尔还下双黄蛋。 青杏在一年后的生产中死于难产,她生下一个丫头,大出血,丫头保住了,自己死掉了。丫头取名小麦,名字也是石榴给取的。 石榴不愿想起那个夜晚,石榴也很少提起那个夜晚。是她刚生完我四舅的第五夜,咔嚓咔嚓的响雷像要把屋顶揭开,一道接一道的闪电像孤魂野鬼在空中张牙舞爪,雨从天上倒下来。男人去县城执行任务没回,她婆奶奶病在床上起不来。小女人在剧烈的疼痛中翻滚着。 我不是一个心里阴暗的人,但我总禁不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揣测着石榴那一晚的心思,石榴那一晚的心思必定是不能平静的,必定是电闪雷鸣、惊涛骇浪的。所有的恶念,所有的快意恩仇必定是兴奋了她,也吓坏了她。石榴最终也必定是在电闪雷鸣般的恶念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不然,哪里会有小麦的出生呢。后来,在小麦和大麦争夺男人,在大麦跳湖死的那一刻,石榴也必定是咬牙切齿的吧?她恨着小麦,也必定后悔着自己在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给了小麦一条性命吧? 孩子生下来是在下半夜,石榴把剪刀在火上烧了,把脐带剪了,那一刻,她心里是有过一丝庆幸的吧?小女人生的是丫头。她把丫头包好放在床上时,发现小女人下身汩汩流淌的鲜血从床上淌到地下,黏黏稠稠的一大片。石榴望着气息渐渐微弱的小女人,望着门外的暴雨雷电,瑟瑟发抖。 石榴背来了她婆奶奶。她把婆奶奶放在小女人床头上。婆奶奶试试小女人鼻息,拽着湿淋淋的她没让她去请大夫。婆奶奶颤颤巍巍地说,运仓回来我给他说,你尽力了,没你事。婆奶奶说了没她事,男人回来也没怪罪她,以后的岁月里,她心里还是隐着歉疚的,她把这份歉疚还债一样还在小麦身上了。 再没有哪个女人拥有像石榴一样值得骄傲的的乳房,再没有哪个女人拥有像石榴一样值得骄傲的子宫。石榴其实是一个小个子女人,身高不足一米五,却是标准的丰乳肥臀。石榴的乳房,像婴儿脸蛋,饱满,细腻,温润,点缀着令人垂涎的红樱桃。石榴翘翘的屁股,像精美的瓷器,洁白如玉,光滑圆润。石榴深藏的子宫像一座王宫圣殿,又像一座春天的花房,时刻孕育着神奇与鲜活的生命。 我姥爷死于一九六零年的那场大饥荒,他死后三个月,石榴又生下他们的第十九个孩子。在十九个孩子中,十男九女。那一年,石榴年方三十五岁,我姥爷四十二岁,如果不是我姥爷早逝,真不知道石榴神秘的子宫里还会孕育多少生命。她的乳房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甘泉,流淌着琼浆玉酿,滋润丰盈着一个个幼小的生命。青杏死后,石榴的乳房同时供养着两条生命。她的乳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肆意汪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饱满硕大。小麦钻在石榴怀里,贪婪地叼着乳头,贪婪地吸吮着乳汁,真正地有奶便是娘。 11、黄河故道鬼故事 牛运仓被选区长是在他回来的那年冬天。遭遇夏天旱灾秋天的蝗虫之后,遭遇日本鬼子二鬼子的血腥洗礼之后,朱家寨人口大减,整个寨子鸡犬不闻,不见人烟。街上晃动着的都是小日本,二鬼子。活着的人贫病交加,奄奄一息,每天都有人冻死饿死。玉米秸秆被磨了吃,高粱秸秆被磨了吃,吃的人肿胀着大肚子哭天喊地哭爹叫娘拉不出屎来。没办法,石榴只好用手抠,我的两个小舅舅都被抠得嗷嗷叫。这时候鬼子给老百姓发了粮食,成袋成袋的白米堆放在街上,只要去领,鬼子就会笑眯眯地放你肩上让你背走。后来鬼子要朱家寨人自己选出人来,替他们发放粮食。牛运仓当选了。 牛运仓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当那个区长,他回家和石榴商量。 刚从街上背回一袋大米的石榴说,选咱当,咋不当,谁给咱饭吃,咱给谁干活。一大窝孩子要活命,活命比啥都要紧,死了说啥都白扯。事实上,当不当区长都不是牛运仓说了算,也不是石榴说了算,不当,怕是连命都保不住。可是,鬼子的大米白面也不是好吃的,鬼子不仅要区长帮他们发粮食,还要他帮着抓人修碉堡,修工事,抬担架,打自己人。 一九四五年夏天,石榴的大儿子二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在失踪两天之后,尸首在黄河故道里浮上来。几天前,他们的爹,朱家寨的区长牛运仓,在小鬼子的威逼利诱下,刚帮小鬼子做了一件事。一个藏在寨子里的八路军,面对小鬼子以一寨人性命为代价的威逼恐吓,牛运仓交出去了。 两个儿子死得不明不白,石榴认准了是有人把她儿子投了河,姥爷说,可不敢瞎说,兴许是孩子自己掉河里淹死的,兴许是二鬼子祸害的,是二鬼子的反间计。哑巴吃黄连,只能咬碎牙往肚里吞,石榴的仇恨只能发泄在一个用麦秸扎的小人身上。石榴亲手埋葬了两个小儿子,和两个小儿子一起埋葬的,还有那个扎满钢针的麦秸小人。 石榴的婆奶奶死于一九四六夏天。老人病得也蹊跷。只说浑身哪里都疼,遍访名医,却看不出啥毛病。石榴找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摇着头不收卦金。没几天,猫头鹰在她家屋前柳树上叫了三个晚上。听着猫头鹰叫,石榴知道阎王爷来下请帖啦,她婆奶奶大限到了。果然,花掉了五亩好田地钱,老人还是撒手归西了。 石榴后来才知道,婆奶奶是保佑她呢,田地少了,她家才逃离了地主成分。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家庭成分成了个人命运的主宰。贫下中农扬眉吐气,贫下中农的招牌像一张畅通无阻的红色通行证,而被贴上地主标签的人家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被批被斗,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有的还为此丢了性命。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参军,招工,招干,推荐上大学,都与他们无缘,他们被骂作地主羔,狗崽子,低人一等。石榴家的成分划分的是富农,即便是富农,后来我十舅想当兵,他体检合格,政审也是没通过的。 那年夏天,发生在黄河故道里的鬼故事,每每听石榴讲起我都会不寒而栗。石榴说,之前,好多故事都是听她婆奶奶讲的。而那年夏天的事,是她亲身经历的。 遵照婆奶奶的遗愿,她死后要埋到祖坟上,牛家祖坟在黄河故道南岸的虞城县,李家祖上是从河南逃荒要饭落脚到河北岸的。为了把婆奶奶安葬到祖坟上,石榴和姥爷一行四人抬着老人的尸首在一天傍晚出发了。 老人的尸首是绑在绳床上抬着的。石榴说,路途远,只能把婆奶奶装病人,不能装棺材,死人住店是犯大忌的。石榴说这主意是她想出来的,把婆奶奶的尸首绑床上,用一块蓝色的棉布单子盖着。床是那个年代独有的绳床,没有床板,代替床板的是纵横交叉的麻绳,老人的尸首深陷其中。傍晚出发,走到黄河故道天挨黑。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过齐腰,原以为两里多宽的黄河故道水面,也就一个多时辰的路程,可是走到河中间过不去了。明晃晃的月亮一下子被天狗吞了,人像走进了狗肚子里,霎时就黑得啥也看不见。水面起了漩涡,脚底下像被什么东西拌住了,对面看不见人,喊人也听不见。石榴说,她大声喊我姥爷的名字,可嗓子卡住了,光张嘴,出不了声。好多只冰凉冰凉的手拉着她的胳膊抱着她的腿搂着她的腰,她着急挣扎,动弹不了。周遭响起了哭声呻吟声,喊疼的凄厉嚎叫,喊救命的疾呼。她好像听到她的两个孩子喊救命,凝神倾听,嘈嘈杂杂中又听不真切。她大声呼喊他们的名字,就是出不了声。直到远处传来雄鸡报晓的声音,天狗逃遁,一切复归沉寂。 犹如一场梦中醒来,大家依然肩上抬着老人尸首,僵立在水中央。 在送葬队伍中,有石榴有我姥爷,另外两个是八路军。八路军借送葬之行,深入河对岸的敌占区摸排情况,没想到遇到了黄河水倒,遇到了鬼打墙。其中一个说是八路军,其实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他吓得灵魂出窍了。上岸后一直神情呆滞,目光涣散,一语不发,走路像僵尸一样机械僵硬。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在回来的路上,回来时眼看到了黄河故道,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地身亡。 石榴说,那个八路军孩子叫黄河水倒拉走了。黄河故道里的冤魂野鬼太多了,她那次也吓得尿了裤子。水倒的故事她听她婆奶奶说起过。 她婆奶奶说,黄河水倒就是黄河里的冤魂野鬼,他们死后像人一样在水里游走,身躯在水面以下,头发飘在水面,碰见过河的人就拉住作替身。她婆奶奶多次警告她,夜里千万别去故道边,看到河水里有东西漂着别去捞,听到人叫你名字别答应,一伸手一答应水倒就把你拉走了。那年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堤之后,一时间河水倒流,淹死了几十万人。黄河中浮尸如过江之鲫,尸体顺着水流往下漂,一摞摞堵在河湾处。一群群大鱼鳖精在水下啃食,咔嚓咔嚓,伴着凄厉的痛苦呻吟,夜里顺风传二里地,让人毛骨悚然。那两年,不要说晚上人不敢走近黄河故道,就是大白天,一个人也不敢。 发大水之后的第二年,都接近秋天了,秋老虎当头,晒得人蔫头蔫脑,村上叫李二撅头的一个老光棍,自恃胆大,和人打赌,要去黄河故道洗澡。是正午,白花花的大太阳头顶悬着,牛运仓和几个年轻人,跟着李二撅头来到故道边。故道里水浅至膝,最深处也不及腰。李二撅头在年轻人的起哄声中走向波澜不惊的河水。没走到河水中央,就见李二撅头身子摇摇晃晃扑扑棱棱,像是和什么人拉扯打架,水面溅起白凛凛的水花花,没及几个年轻人反应过来,李二撅头就没了影子。几个年轻人往回跑,腿转筋,脚打拐,四肢不听使唤,爬着滚着,嚎得没人腔。 一个叫羊屎蛋的孩子,被家里人抬回家,浑身哆嗦得按不住,眼瞪得牛眼大,手在空中乱抓乱挠,嘴里不住声地喊着有鬼有鬼,叫得那个瘆人,当天夜里就死掉了。牛运仓那次也吓破了胆,一直昏迷不醒,是他奶奶请巫婆跳了大神,傍晚拿耙子一次次去故道搂魂才醒过来的。 其时,牛运仓爹娘刚给石榴爹送了定亲礼,石榴后来和牛运仓开玩笑,你那时候要是被鬼拖走了,我算不算你的寡妇?我要不要给你守节等着立牌坊? 抬着婆奶奶的尸首住店也遇到大麻烦,单说是个病人店家都不让住,怕沾惹晦气,姥爷找了好几家,都被撵出来了。石榴一次次地陪着笑脸,好话说了一箩筐,付了双倍价钱,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住下了。 石榴说,她们带婆婆是去还愿的,只是,婆婆路上不能见生人,不能说话。 石榴又走进婆婆,拍着床沿,大声说:娘,您听见了没?回头,咱来时还住这里,咱得好好谢谢这好心的店家! 在这次送葬之行中,牛运仓成功掩护了八路军,是立了大功的。事实上,牛运仓在整个抗战时期都是立了大功的,他名义上是伪区长,也正是利用了这个身份,他不止一次地给八路军通风报信,给八路军筹粮,他还亲手掐死了一个日本鬼子,救了一个八路军的命。 那个夜晚,在一个巷子口,一个鬼子追一个八路军,被他碰上,他一个绊子鬼子趴下了,他扑过去,骑在小鬼子的身上,死死掐住了小鬼子的脖子,小鬼子反手扯断了他新崭崭的夹袄袖子,咬掉他一截手指头,我姥爷和那个八路军一起把小鬼子埋了。他还带头给八路军支援了三千颗子弹,二十杆长枪。 石榴记得那个夜晚,那个夜晚家里来了八路的人。八路要牛运仓筹粮食,带头捐枪支弹药。石榴私下里跟男人说,二鬼子七路皮,就是她娘的一窝子遭殃军,见鸡逮鸡,见羊牵羊,见猪捆猪,见牲口拉牲口,拉不走的也给杀了吃肉。马三家里的一头青驴被杀了,一头黑老犍被拉走了。你再看看人家八路军,到了村里也不进老百姓家门,住在树林子里,拿老百姓一根针都给钱。打鬼子也不含糊,都抢着往前冲,不像那帮龟孙二鬼子七路皮,鬼子一来就变成缩头乌龟了!小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咱得给自己留后路。 可惜后来没人出来给姥爷当证人,证明他不是汉奸。当然,身为区长,他也干了不少坏事,愿意不愿意,他都得给日本鬼子、给二鬼子送信、筹粮、抓壮丁。他当区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不仅为此失去两个年幼的儿子,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没被定性为汉奸,但在朱家寨人眼里他就是汉奸。没谁公开说,可是平日里人们躲瘟疫一样躲着他,也躲着他们一家老小。一旦朱家寨认定了他是汉奸,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汉奸这两个字像楔进他皮肉里的钉子,像沾在他家门楣上的狗皮膏药,拔不下来,揭不下来。石榴说,幸亏他早饿死了,不饿死,后来也得斗死他,整死他,他活着,只会拖累这个家,给这个家带来更多的祸灾。 作者:耿雪凌,女,山东单县人,乡镇干部。山东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山东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小说散见于《湖南文学》《短篇小说》《山东文学》《牡丹文学》《齐鲁晚报》《深圳晶报》等省内外报刊杂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爱情不说话》。 往期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引子(代序)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1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2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3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4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5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6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7 长篇小说:石榴花开-连载8 耿雪凌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tz/2352.html
- 上一篇文章: 关于开展县树县花评选活动
- 下一篇文章: 民族团结一家亲兄弟携手共创甜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