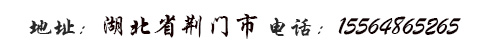有些人来了一阵子,你却念了一辈子
|
文 夏芃 (全文余字,大约需要10min,适合慢读。) 年的夏天,是有些人一辈子回不去的梦牵魂绕。 梦里有人在说话。木门轻轻叩了几下,伴随着一句“有人在吗?”见无人应,又敲响了一点儿。 午后酣睡的秀秀被惊醒了,她伸个懒腰,从竹躺椅上坐起,将散乱的头发往耳后压了压,便起身趿拉着布拖鞋去开门。步子踉踉跄跄的,呵欠连天。 嘴里含混嘀咕着:“大中午的谁啊?”抬手扒开院门的小木栓,先是探进一个理着平头的脑袋,随后,一个瘦高个的年轻男子从门后闪了出来,横在她面前。 秀秀后退两步:“你是谁啊?走错门了吧?”那人抬起胳膊擦了额上的汗,冲她笑道:“你家租房子吗?” 秀秀一甩辫子,扭头朝院子里大喊:“伯伯,妈妈,你们出来,有人租房子。”没多会,出来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问了几句,把年轻男子给领了进去。 秀秀家是青砖平房,一排五间,除了一家人吃住和放杂物,伯伯还自己动手在西面挨着厨房的地方砌了间厢房,一直没派上用场,就空在那里。 他们家在县城边儿上,出了门不远有个小集市,周边乡镇的村民买点针头线脑、日用百货什么的也常来这,人来人往,热闹的很。 偶尔有进城谋活的人过来找地方住,她伯伯心眼活泛,就想着把那间空房租出去,也给家里贴补点收入。 因此早早在街坊邻里间漏了口风,要是有人来这片儿问租房子的事,就帮忙给指引下。想必这年轻人就是这么找过来的。 绕着院儿看了一圈,觉得比较中意。双方谈妥了租金,一月三十块钱,管热水不管吃。过了一天,他把一床凉席一床薄被扛进了西厢房,就算在这落脚了。 第一天傍晚,秀秀一家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吃饭,年轻人从外面进来,妈妈叫了他一句:“吃了没?一起吃点吧!”他笑笑说:“不用,我吃过了。”声音有点沙哑,好像很疲惫似的。 汗衫后面有一大块汗印子,肩膀上也有不少泥灰。他没停脚,走到自己房里提了个桶出来,肩上搭块毛巾,到水井边汲了一桶凉水,妈妈站起来说,“我给你倒热水去。” 他摆摆手,提着桶转到房子背面,只听得一阵阵水花从高处浇到地面的声响。伯伯说:“这娃怕是找到活儿了。”秀秀插嘴:“找啥活?”伯伯喝了口稀饭,咂摸着道:“十有八九是在东头那个厂子扛货。” 秀秀没吭声。第二天早早起来,在水井边搓衣裳。弟弟去学校期末考试了,伯伯上班,妈妈在商店包了个小柜台卖布料。 年轻人准备出门,秀秀叫住他,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从井台上拿起一个烧饼递过去。他怔了下,接过去咬了一口,也不说谢,似笑非笑的样子。 秀秀问他:“你是在东头厂子干活吗?”他说:“是啊!你咋知道的?”秀秀甩了甩头,露出一口白牙:“我瞎猜的。”两条麻花辫搭在圆鼓鼓的胸前,阳光透过树叶照在她的脸上,留下窸窸窣窣的光影。 过了三两天,没那么生分了,才知道这人叫刘家良,家住离县城二十多里地的村上。他刚高考完,在等录取的消息。家里不宽裕,趁着这段时间出来找活,多少能挣点。 秀秀的弟弟小江刚上初中,班里的落后分子,期末数学才考了三十多分。对着老师留的暑假作业抓耳挠腮,家里没人能帮上忙。 秀秀虽然读完了初中,人也不笨,可是拿起书本就是一团浆糊。伯伯厂子能安排子女上班,已经给她报名排队了。不过家里经济还算宽裕,她刚满十八,妈妈也不舍得她这么早出去做事。 刘家良有天下班回来,看到小江苦着脸唉声叹气的样子,过去点拨了他几下。小江高兴坏了,接连几天缠着他,把暑假作业全写完,便跑去乡下外婆家撒欢了。 工厂中午管饭不回来,一天也只有早晚能看到他。夏天太阳出的早,秀秀怕热,总是早起趁着凉快把全家人的衣服洗了晾晒好。上午没事,就坐在葡萄架下绣花纳鞋垫。 她家的院子十分敞亮,伯伯在院子里种了石榴,兰花,还有好几棵橘子树。橘子树上缀满了比手指头大不了多少的青果子,一嘟噜一嘟噜,叫人看了喉咙里直泛酸水。 刘家良出门,有时候给秀秀说一声,有时候径直就走了。说的时候秀秀有点心不在焉,绣花针一下就戳到手指头上,渗出血,白布就染上了点点红色。 她在有血迹的地方,用红丝线绣一朵花,血就盖住了。有时,她也会闷闷地坐上半天,盯着树上的石榴花发呆,或者就着微醺的风打个盹儿。手上的绣活儿老是出错,拆来拆去的,进展慢了许多。 有一次,秀秀扬起脖子,故意问他:“刘家良,你能不能考上大学啊?”他挑挑眉毛,嘴角微微笑着:“不知道啊,还在等通知呢!”。 “那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呀?” “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呗!” 他满不在乎地说着,声音里却有一丝发颤,边说还边用右手摸了下鼻子。秀秀知道他这是紧张了,他一紧张就喜欢用手摸鼻子。 忙收起脸上的戏谑,低下头,又偷偷拿眼角打量他,见他没生气才放下心来。一个星期天,伯伯和妈妈去乡下走亲戚了。 太阳又毒又辣地高挂在天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被晒的蔫蔫的。秀秀浑身燥热不得劲,中午饭也不想做了,解开小褂子,只穿了白色的背心,一只手摇着蒲扇,另一只松松地搭着扶手,在葡萄架下的躺椅上闭眼小憩。 院子的小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人跑了进来,秀秀来不及把褂子套上,只慌忙用蒲扇盖住胸前,羞红了脸。 刘家良侧过头去,急急往屋子里走,秀秀穿好褂子,又羞又臊,一时不知怎么才好。过一会,刘家良咳嗽两声,走出来,站在石榴树下,大声说:“我今天要回家一趟,明天再过来!” 秀秀有点奇怪:“你回家干啥?”他把手从背后拿出来,扬着一张红色的纸道:“我考上大学了,回家给我伯我妈报喜去。” “是吗?”秀秀听到这个消息一高兴,忘了刚才的尴尬,跳起来就要去抢他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几缕头发从辫子里跑出来,被汗浸湿了搭在脸上她也没发觉。 刘家良说这个大学在遥远的北方,忽然想到长这么大,她连安庆城都没去过几次,心下颓然。家里开满花的院子,散发出古旧木头气味的老街,还有那几条青石板的小巷,是她最熟悉的风景。 读书的学校离她家只有三百米,下课还可以跑回来喝个水。放暑假时,她会和小江一起去乡下的外婆家住一段日子,和表亲们一起摸鱼捉虾,采莲挖藕。 外婆家临着龙山湖,风景就像中学语文课本里写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她眼睛里的光渐渐暗下去,抬起头看天,阳光却刺得她睁不开眼。 在那双手圈住她,温热的唇覆上来时,竟毫无察觉。她吓傻了,一动也不敢动,脑子里一片空白,任凭他越抱越紧,他的舌头撬开她的牙齿,与她的卷在了一起。 终于,她的身体开始颤抖,一只手隔着衣服掐他的背,一只手还僵硬地悬在半空中,捏着那张红纸。 刘家良把她抱到了西厢房,关上门,只垫着一张席子的木板床硌得她生疼。明明她是怕热的,可此刻她却不受控制地想贴住那个滚烫的身体。 小背心被推到胸口,露出一对圆润饱满的小兔子,他用手捂住这对兔子,把脸扎进去。她的小碎花裤头遮住的地方被顶得生疼,喉咙里却不自觉地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 午后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唱着,石榴树的影子变长了。他想扯下她的短裤,她却用手死命地护着。于是他腾出一只手去钳住她,另一只手来拉扯。 两人手上使着劲儿,嘴上却是一刻也不舍得分开。最后,他胜利了,她的花短裤被撕下来甩在了床角。 他急不可耐地想冲进去,可是却像有一道看不见的门,他越是心急,越是找不着开门的机关,她却被他一次次横冲乱撞弄痛了,又害怕恐慌,眼泪便出来了。看到她的泪,他一惊,抖抖索索地,一下子清醒过来。 天快擦黑的时候,伯伯和妈妈回来,她却还没有做饭,一动不动地坐着,病恹恹的样子,妈妈看她不舒服,便也没责怪她,自己去炉子上下了一锅面条。 吃面时,她还没缓过来,只喝了几口面汤,告诉他们刘家良考上大学回家报喜去了。感叹了几句,大概一天赶路累了,他们吃完洗澡早早熄灯睡下。 秀秀在床上辗转反侧,小电风扇呼呼吹出来热风。她索性起来,蹑手蹑脚地打开门到院子里坐着。是夜,蚊子都躲起来了,凉风习习,送来若有若无的兰花香气。 秀秀托着腮帮子看天,天上有很多星星,有的近有的远,眨巴眨巴着眼睛。刘家良的眼睛也是亮亮的,藏着星星。 她仰着头琢磨着,想找到他们说像个勺子的北斗星。北边是刘家良的家,这会儿不知他在干啥,会不会也和她一样睡不着呢?她低头,一个人影在地上。再一抬头,原来是棵树。 院墙外有咔嚓咔嚓的脚步声,她疑心自己出了幻觉。细听片刻,果然是幻觉,不过是风移花影动罢了。 翌日,秀秀睡得死死的,直到妈妈敲窗户叫她。她起来,觉得眼睛有些不适,对着小镜子照,一晚上没怎么睡,又红又肿。 妈妈以为她还不舒服,叮嘱她吃了饭回屋歇着。起来打了盆井水,用毛巾拔了凉水敷脸。又换了件粉色的新褂子,倒衬的她唇红齿白,病色全无。 眼巴巴地在院子里坐了一上午,树底下有个蚁窝,蚂蚁进进出出,也不知有没有听见她的呓语。 吃过午饭,照常在院里躺椅上小寐。迷迷糊糊中听见敲门声,谁还在说:“有人在吗?”她连忙跳起来朝院门口跑去,院门是开的,却不见人影,原来是在梦里。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刘家良回来了,还带来一兜子鸡蛋。妈妈在跟前,两人没得着单独说话的机会。伯伯下班带回来一瓶酒和一些熟食,妈妈炒了鸡蛋,还做了过节才有的山粉圆子烧肉。 他陪着伯伯喝了点小酒,边喝边拉家常。秀秀不作声埋头吃饭,几次夹菜的时候两人的筷子碰到了一起,刘家良笑笑,她却莫名地有些恼,索性不夹菜了,光扒拉碗里的白饭吃。 刘家良说待不了多久,快开学了。她心下一酸,只道吃饱了,便放下筷子回屋。一进屋,她趴在床上,把脸扎进被子里,不一会,洇湿了一片。 半夜起来上厕所,他屋里的灯还亮,她怔怔地看着,想起晚饭前后他不冷不热的样子,叹了口气。夜里很静,月光铺在地上,给青砖蒙上了一层柔纱,掉落的花瓣点缀着。她的影子在地上拖得长长的,像一个感叹号。 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他刚来的时候,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一天天的变得熟悉,而现在,却有意地疏远起来。 他晾晒在绳子上的汗衫肩膀处磨破了,秀秀悄悄收起来补好又搭回了原处。 傍晚他收衣服的时候看到了,望向在井台边洗菜的秀秀,嘴巴张开,想说点什么,到底又没说出来。她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石榴花谢了一些,葡萄熟了,妈妈摘了几挂叫秀秀洗了给刘家良端去。秀秀放到他屋里的小破桌上,他正在收拾东西,也就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 她明白他这是要走了。天气凉快了些,他床上还铺着席子,床脚还有半盘点剩的蚊香。 她蓦地跑出去,不一会又进来,将一个纸包放在了床上。 他没说话,嘴角淡淡勾起,似乎想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终是挤不出来。她定定望着他,相顾无言。 秀秀走后,刘家良打开那个纸包,是一双鞋垫。鞋垫上绣着火红的石榴花,就像他们初见面的那天院子里开的最盛的那朵。 那天的秀秀,穿着红色的短褂子,露出两节嫩藕似的手臂,几缕头发从麻花辫里跑出来,黏在雪白的脖颈上。 她脆生生地说:“你是谁呀?你走错门了吧?”黄灿灿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在那个盛夏的午后,绽放在他眼前。 一步花开,一步花落。就像天空里的那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终归,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只是,每一个石榴花开的夏天,不知是否还有人会旧梦重温。 注:封面选自丰子恺作品集 夏芃 有时看图纸,有时写故事; 既能在烈日下行走,也愿在温柔的晚风里徜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zz/6910.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闻早八点年12月15日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