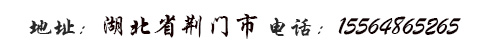厦门通信三
|
《厦门通信(三)》 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例如这里的报纸上,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训霸占公地”的笔墨官司,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训何人,曲折怎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诬也;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治睁大着眼睛对我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质之高明,未识以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称病辞去了。百无可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而来的,现在不到半年,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叫他们怎么办?这实在使我夹脊梁发冷,哑口无言。不料“思想界权威者”或“思想界先驱者”这一顶“纸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误人子弟。几回广告(却并不是我登的),将他们从别的学校里骗来,而结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万分抱歉。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记事,将学生们拦住。“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哲学,似乎有时也很是误人子弟的。 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沈》印出。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请你印。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及至到了这里,看看情形,便将印《汉画象考》的希望取消,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其实是已经可以走了,但看着语堂的勤勉和为故乡做事的热心,我不好说出口。后来豫算不算数了,语堂力争;听说校长就说,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并不欺骗。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钩沈》的意思也取消,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语堂是除办事教书之外,还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尽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开会议,连国学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顾问,据说是所以连络感情的。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为什么研究国学,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顾问的绳,将他络住?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兼士又已辞职,所以我决计也走了。现在去放假不过三星期,本来暂停也无妨,然而这里对于教职员的薪水,有时是锱铢必较的,离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来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经出题考试,作一结束了。阅卷当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请暂勿寄来,待我有了驻足之所,当即函告,那时再寄罢。 临末,照例要说到天气。所谓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评家指为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声明:并非如此。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苍蝇不见了,蚊子间或有之。 夜深了,再谈罢。 鲁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海上通信》 小峰兄: 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他不懂。他也能说几句日本话,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笔谈,才知道他是丝绸商。我于丝绸一无所知,他于丝绸之外似乎也毫无意见。于是乎他只得睡觉,我就独霸了电灯写信了。 从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闲空,给《唐宋传奇集》做一篇后记,准备付印,不料现在又只得搁起来。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长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新说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新近还听到我的一件罪案,是关于集美学校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现在因为反对校长,闹了风潮了。先前,那校长叶渊定要请国学院里的人们去演说,于是分为六组,每星期一组,凡两人。第一次是我和语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书来迎接。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场。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 鲁迅。一月十六夜,海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gs/8196.html
- 上一篇文章: 统战实践bull亮点借党派之力,
- 下一篇文章: 大调曲子音乐考察与分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