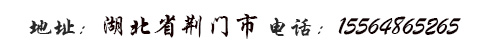时间能慢点吗
|
哪个医院白癜风能治愈 http://pf.39.net/bdfyy/ 时间能慢点吗? 澜湄河 家乡往事(1) 祥云的天气依然干燥而清凉,但是比往年热了很多,83岁的母亲身体比我预想的要好,还能做饭,在院子里种菜。秋天的庄稼地大部分的玉米棒子已经采收,枯黄的杆子挺立在那里,没有完全枯萎,一副功德圆满骄傲的样子,把路边仙人掌上蓝色的、粉色的牵牛气得焉巴巴的。 牵牛花无力的耷拉在仙人掌刺上,显示了对初秋的无奈。 我走到低矮一点,背阳的山坡,折了一根还有点绿色的玉米杆,嚼了嚼,酸的。又找了一根有虫眼,褐色的包谷干,甜的,但带有那种象腌菜坏了箜(kong)味,小时候是美味,现在觉得不那么好吃了。怎么嚼,也没有水分,只有甜味和满嘴玉米杆渣。 孩童时牛棚中的老水牛也是我这样嚼着,眼睛无神地望着远方,明天是否会下雨?我蹲着的嚼玉米杆那状态跟牛差不多。 低矮处有一小部分水稻田,不知道还有蚂蚱吗?以前人还没走到,就能听到嗖嗖嗖的一片跳的、飞的,绿色的、淡黄的蚂蚱往远处躲,谷丛里,小草中,田埂下。躲在那里,瞄着你,看看你有什么动作?当然还有几只强壮的蚂蚱直接飞到玉米杆叶片上看着你,问你,你能耐我何? 走近的时候看到有两个老人在剪稻穗,男的带着宽边竹帽,女的裹着头巾。背着竹篮子。 以前是竹篾编的竹篮子,现在还叫竹篮子,其实是塑料或者纤维的绳子编的。稻田中已经见不到蚂蚱,是生物防治还是其它办法会让这么多的蚂蚱找不到踪影。我还是有一点点失望的,童年的我傍晚爱去捉蚂蚱,每天都能捉到一到两斤的鲜蚂蚱,回家后加一点点水,把蚂蚱放铁锅里,盖上竹盖子,几分钟打开后就能闻到蚂蚱和青草焖过的香味,绿油油的蚂蚱变成了金褐色,放着亮光,会让我有流口水的冲动,捡去蚂蚱还没有变成粪便的稻叶坨,晾晒在厦空的青瓦上。做完农活的父亲喜欢靠在坎子上的木柱子上,用母亲脆香的油炸蚂蚱下一小杯酒。 父亲望着天空盘算着明天的农活。而我也在院子里面玩着用田泥搓圆阴干放在煤炉中烧过的泥珠子,有黑、有灰、有黄、褐色。彩色的我最喜欢,用它弹出去,把其它色的打到不同的洞里面。 院子里面的灯光很暗,很大的院子母亲只舍用15瓦的钨丝灯泡,所以把我小小的身影拉得又长又宽,还模糊,分不清头和身子。 父亲坐在坎子上,我胆子就大了许多,敢跑到门外那几棵高高桉树下面,黑漆漆的树中去捉那到处乱窜的金龟子。桉树叶我跳起来能摘到都几乎被我采完了,用来上厕所时擦屁股,我不喜欢用圆石头。我那几个伙伴都不爱上厕所,他们总是拿几个石头蹲田埂上,擦了屁股打远处的老鼠、玉米杆上叶子上的虫子,或者过路的抬着虫子的蚂蚁,嘴里还说着“你们力气大把我的石头也抬回去吃”。夜晚的玉米地总是很黑,有时还有刷刷的响声,让我害怕,我担心里面会有一个什么东西跑出来。 桉树对面厕所旁有一棵花椒树,整个夏天树干上都爬满了黑幽幽的毛毛虫,上面细的枝干也东一个西一个的趴着带银环的毛毛虫,还有两个角抬起来,有时候还能看到它抬头东转西转的在树枝上绕细丝。最恶心的是树叶上全身都绿色的一种虫,一动不动,还象蚂蚱一样长着壳,在身旁吐很多白白的泡沫。我有时候会用石头远远砸它们。 母亲从来不管它们,她总是摘那最大的花椒来吃,然后採一部分晒干留着后面冬春这几个月用,瘦的、小的母亲就让它们干后自己脱落。 稻谷 夕阳把安静地的土地盖了一层秋黄,远处的乡村被远山和农田着包围着,显示了城里少有的静谧。 两个老人离的很近,剪着稻穗,现在让稻杆直接腐烂还田。 以前用镰刀割稻谷,把稻杆留到脚踝高,稻杆和稻子都朝一个方向整齐摆放,留几天晒干了挑回家。 每家的稻田基本一天要割完,互相换工,不给工钱。今天你家的,明天我家的,根据稻子成熟情况先割哪家。割稻子的人带着草帽,弓着腰,会分开一段距离,每人割一趟,远处看去头脸都是埋在稻穗中,人就特别累, 割稻子的人也很多,有的累了就直起腰,用手捶捶,接着弯下腰努力割,都不想被拉下。也有割得快的,把两边的拉下了一段,直起腰,摘下草帽往脖子、脸上扇风,转过身来大声的唱两句略带轻佻的歌给后面男男女女听,然后坐下来拿出铁烟盒,卷一根土烟,划过的火柴梗被弹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入前面的稻田中。 家里都是母亲记工,母亲没有文化,不会写字,但她记忆力很好,现在80多岁了还能给我讲原来村里面的好多往事。劳动力少,不给工钱,换工。还不了工的可以在冬、春季给人家盖房子,或者给小麦苗地浇水、蚕豆地除草。 晒干后的稻子白天被父母们一担担挑回家,也有用手推车拉回家的。傍晚父亲换了一个一百瓦的灯泡。 母亲借来了几个大大的竹筐,感觉有我高,父亲和叔叔们把稻穗尽力的从肩背后往前面竹筐沿边上砸,母亲和孃孃姐姐把扎好的一把把稻子递到他们手上。 谷子滚落框中,有散落的谷子往远处飞去,那几只得意的公鸡欢快地到处追捉谷子,无聊的我有时候追着打它们,不给公鸡吃。母亲不让我打那些母鸡,还有小鸡。说它们下蛋给我们吃,要让它们吃饱,母鸡吃饱了就爱趴在院墙边那几棵绣球花树旁,中午它们都在打瞌睡,偶尔还伸出头啄啄土和其它腐草,也不知道它们是吃土还是吃虫子。 剩下的稻杆又长又直又粗没有折断被摆放在墙边,老人们一小捆一小捆地摆在墙角照不到太阳的地方晾干,剥去皮,放在木板楼上。粗的硬的做成了草帘子,(跟今天席梦思的功能一样),双层中空,夏天透气凉爽,冬天柔软保温。细的软的做成了草席,摆在草帘子上,加一个毯子或者一个薄棉絮,一个多次被缝补过的被单,一张窄床装着我温暖而瞌睡的童年。 大部分的稻杆变成了稻草,母亲把稻杆铺在平地上,晒几天,用镰盖(用一根木棍做手握的杆子,顶部打洞,在用竹子编10-20cm宽,长1米左右长方形竹编,固定在木杆的洞中,可以任何一个方向活动)把在竹筐上砸剩下的饱的、瘪的谷子打下来,用簸箕不停的上下簸谷子,饱的最后磨成了米,瘪的被粉碎成了米糠,米糠喂猪。打绒的了稻杆垫猪圈。 绒绒的稻杆温暖着我家那几只小黑猪仔。它们竖着直立的小耳朵,摇着小尾巴,东拱一下,西拱一下,有时候还打两个滚,然后跑到猪妈妈那里吸两口接着去拱稻草。猪妈妈爱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不知是真睡着了,还是在享受着天伦之乐,偶尔还哼两声。最小的那只小黑猪嘴喊着乳头,背靠着母亲的乳房伸着两脚进入甜甜 水库 穿过稻田,没有看到蚂蚱在跳,一只也没有见到,稻田旁不知谁家种的几亩花椒地,粗壮的树干,褐色的枝条,绿油油的叶子又厚又亮,地上被铲得干干净净,裸露的土地被太阳晒得散发出热气,陇沟潮湿柔软,花椒树横竖都排的很整齐,有几陇还布置着黑色的地膜,这几年农业科技下乡,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按技术人员要求种植管理出来的。 水库的大坝两面都都用方块石头覆盖了一层,长满了矮草,坝埂路两边都拉上了铁丝网,牛、马、毛驴再也不能在上面吃草了。 大坝下面的水井依然还在,只是井上面的水泥小房子屋顶已经破烂,墙面斑斑驳驳,还留下几个洞,井里面已经没有水,铺满了石块,杂草等垃圾。这是以前我们小村三四十户人家的主要人畜的饮水源。 “桶摆着,我们几个伙伴要去走走,你们几个去坝那边水库里看看人家给钓到大鱼。”青姐交待我们。 仿佛就在眼前,小时候,或者说也不是太小,已经是小学一年级。 从家到这水井也就两公里不到,一路过来灌溉用的水沟很宽,沟两边是一排高高的桉树或者是弯弯的柳树。 跟母亲一样年龄的几棵柳树树干弯在水面上,柳条垂入水中,偶尔还有一些小鱼围着柳叶嘴一张一翕吹泡泡。水沟边长满了红浆草,开着粉色的小花,很多红浆草叶片背上有密密麻麻的黑点,青姐告诉我们那是癞蛤蟆的儿女在那里睡觉,醒了就变成小蝌蚪。 有的红浆草叶杆还挂着一串串泡沫,姐姐们告诉我们那是大麻蛇的吐的,别碰,有毒,当然我们也经常看到小蛇从沟里面水面游过,尤其是中午太阳照得非常热的时候。 我们几个小伙伴是不敢独自来挑水的,我们害怕,怕蛇,也怕沟的尽头那深深的绿,总感觉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会跳出来。 母亲她们也不让我们自己来挑水,害怕我们滑入那沟里,交待好姐姐们带我们,她们的是大桶,我们是小桶,让我们走前面,她们在后面看护着。 水库的从农历四月份到九月份水面会浅下去好几米,其它月份都是满的,离坝埂面就两米左右,那时候钓鱼的人很少,水库管理所不让钓,只有偶尔的几个老头从城里面骑自行车下来钓鱼,听姐姐们说都是城里面离休的干部,官大,跟水管所的人熟悉。 我们都认为他们真无聊,城里面有那么多好吃的,还来这里干坐着吹冷风,比鱼好吃的东西有许多。 我们喜欢跑到水库靠山边平坦地方去玩,有两三平方公里,那才是我们的乐园,那里有浅浅的水面,各种小花,还有很多的牛,马,毛驴,骡子,对面的山上是梨园,苹果园,桃园。我们都想骑马,但是我们几个跳起来也上不了马背,也害怕它踢我们,都不敢靠近。毛驴很温顺,我们跳起来爬在上面,不敢坐起来,担心掉下去,每个孩子都跳上去,爬着赶着它走一小段路,一个一个轮着来,下来的时候胃部、肚皮被硌得很疼。 看到大姐姐在坝埂上向我们挥手,离太远,听不到她的喊声。我们知道该回去了,比赛一般往回跑。 坝坡是哥哥姐姐们聊天的地方,东一颗西一颗核桃树,高大粗壮,树干都跟我们腰一样粗,下面是各种杂草,各色的小花。还有一丛丛的石榴树,坝坡上生活最惨的是梨树,粗粗的树干,凌乱的枝丫,从它满树的梨花到结出小梨仔,就被一批一批的孩子折磨着,我们把梨花折下来插入柳树条编的帽子上,编制一条美丽的紧箍咒,象孙悟空一样拿着棍子乱舞;梨仔被我们採下来放入细竹筒中比赛看谁吹的更远,或者吹在女伙伴的头发上,比我们小的男孩子脸上。大一点或者强壮一点的男孩子也是这么欺负着我们。 不知道这里的成熟的梨是什么味道,我啃过的都是厚厚的皮和深深的涩味。核桃树和石榴树保存完好。核桃树太高,我们爬不上去,成熟的核桃被我们用竹竿和石头打下来,用石头砸开坚硬的外壳,里面果肉很少,要用坚硬的小棍子才能扣出尝一下味道,跟老鼠相比我们没有它们的耐心,所以大部分核桃可以享受阳光和雨水,成熟后自然脱落。 石榴树我们不爱招惹它,刺太多。石榴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被採下来打水沟里面的小鱼,或者去水库里面比赛看谁扔的远,也喜欢看石榴花扔水库里面几条鱼儿抢食的过程,树尖上的石榴成熟后被我们用棍子打下来吃,是酸的。 爬过坝埂水库看着小了许多,水也很少,只是一个大大的水塘,空地上也没有了以前到处奔跑的马匹,安静的毛驴,也没有了以前的繁花密草。 新建的昆明到大理的高速公路、铁路都横穿了水库,水库后面的小山上已不在是满山的桃花、梨花,绿油油的小山包变成了一排排的厂房。 肥料厂、塑料制品厂、锌铝冶炼厂把这水库包围的死气沉沉。 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重合,农历十七的月亮无力地爬过了坝埂,冷凉的月光没有了往日遐想。 稀疏的钓鱼的摩擦车声渐渐远去。 过几天我又要走了,二十多年不经意间西双版纳变成了我的家乡,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感觉我只是曾经来过。 景洪没有遍地枯草中的冷凉秋天,当然它也没有我曾经的童年。 .10.1-18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hj/6825.html
- 上一篇文章: 石榴盆景养不好那是没有掌握技巧,这4点关
- 下一篇文章: 风水先生告诫孙子ldquo门前种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