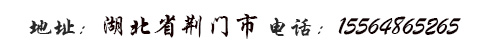北京有个哥
|
1 大自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化腐朽为神奇。 就在一个月前,抬眼望去,偌大的铁炉塬还是万物萧索、天地混沌、长夜漫漫;铁炉塬常见的各种鸟儿、野兔、野鸡之类也不知栖居在了何处?田间的麦苗儿也像随意散落在黄土中的柴禾,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着。水渠里,塄坎上胡乱的堆放着一簇簇、一堆堆被雪霜压塌了的上年的陈旧禾杆;村前屋后,光秃秃干枯的树杈上星星点点的摇曳着几个孤独的鸟巢,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旷野里,偶尔能见到有农夫在田间小埂上无精打采的踱着步子随意溜达,一个或两个摇尾乞怜的小狗紧随身后,这大概是荒寂的土地上唯一让人能感到有动感的生命迹象了…… 而今,春风徐徐吹来,几场春雨过后,气温虽飘忽不定,但人们却在不知不觉间忘记了寒冷的滋味。各种各样大的、小的树枝纷纷吐出了泛黄的嫩芽儿,继而变为淡绿、深绿,一天一个样。花儿也竞相吐蕾,想尽快的装扮大地;田间的麦苗更是迫不及待了,争先恐后卯足了劲儿蹭蹭的开始起身了。于是,整片整片的绿色、粉色就呈现在人们眼前。透过麦苗厚实的叶子,我们看到了大地在把她拥有的乳汁和营养,无私尽情地填喂着庄稼和果树,于是,大地上的生命日见茁壮和精神。 春天来了,春天的感觉真好! 哥推着车出现在村东小路上时,我正挎着小蛋蛋笼在村东的麦田里,手拿小铲子跟着一伙大孩子在为自家的小猪挑草。 远远的望着通往渭南的那条乡间小道,一个穿着军装的人缓缓地向我们村子这边移动,人影渐渐变大,面容也愈发清晰了。 “那人像是三江哥,是的,三江哥回来了!” 本家的比我大8岁的堂哥的眼力真好,很远的地方居然能认出那人是哥,指着远处大路上的哥他激动而惊喜的对我说。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群孩子便放下手中的草笼大呼小叫的向小路上奔去,不一会便围住了哥问长问短。哥便将随身携带的很稀罕的洋糖(水果糖)散发给小伙伴们。 我瞟了一眼传说中的哥,心里有点怯生,不敢上前,因为我头脑中根本没有哥的印象,虽然我断定那人一定就是我在外当兵的那个叫“三江”的哥! 哥被乡亲们围着,大概也不认识我了,反正我不认识他。也许是顾不得和我搭话,我则一扭头迅速向家中奔去,为的是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最短的时间告知父母。 一路小跑回到家,见母亲正在扫院子。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喊着:“妈,我哥回来了!” “你哪个哥回来了?” “我三江哥!” “胡说,就没捎信说要回来呣!” “就是回来了,走到火罐树哪里了!” 就在我努力向母亲解释我没有撒谎的当儿,哥推开了带有窑窝的单扇老式庐门。 看见母亲,哥只叫了一声妈便泣不成声了,他的双腿在发抖,且渐渐的变软了,手中推着的借县城舅家的自行车一忽儿便滑倒在院子里,而母亲手中的扫把同样跌落在地上……,只有一旁茫然而不知所措的我在好奇的看着这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娃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呢?”母亲嗔怪地说。 “走,快回屋里歇息,甭哭了,回都回来了还哭什么?”母亲劝慰着哥,而我分明看见她的眼角也汪着清澈的的泪珠儿。 哥于是用手背擦了擦眼泪,终于破泣为笑了! 原来,哥是写了信的,只因为信走得慢,从北京邮回来需要七天才能到,而人回来只需两天。就在亲亲邻邻得知哥回来了,纷纷到家来看望的当儿,会计送信来了。因了这个差池,我们家演出了一出人间难得的惊喜剧,惹我这个不明就里的小孩子对当时的场景纳闷了好几天,至今想来还仿佛昨天的故事,记忆是那样清晰。 2 哥是我的三哥,比我大15岁。在我4岁时,部队来征兵,哥辞掉了大队会计的工作报名参了军。此前的有关哥的故事都是听母亲说的。 哥上中学的时候正值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其时,取消了高考升学制度,整天串联武斗,他也曾作为学生代表到北京去串联,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确实是风风火火,但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也没学到什么知识,而一家老少五六口人却要吃要喝。当时,大哥一家已分家另住,二哥在西安无线电工业学校读中专,四哥和我都还是个孩子,父亲在外谋生,家中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挣的劳动日少,成了透支户,每年连口粮都分不够,眼见这种艰难的日子难以为继,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16岁的哥依然决然的退学了。 刚开始,他每天天不明就起床,磨快了镰刀,带上草笼和绳索,就下西沟去了。为的是给产队的耕牛割草挣工分。每天喝着泉水就着干馍,忍受着蚊虫叮咬,毒刺扎身累死累活到天黑,他肩上搭着湿透的衣服,居然每天从沟里背回来一百多斤青草。按十斤草一分工的规定,居然能挣十几分工。于是,生产队的青壮劳力不淡定了,因为一等劳每天才挣十二分工。很快,生产队改规定为二十斤草记一分工。为此他去和队长理论过,但无济于事,因为众人都看不到你下的苦,而红眼病却是除不了根的人类疑难杂症。 打墙,伐树,出圈,拉石头、修水利,打夯,一个16岁的孩子干什么活都舍力,半年下来,本来就单薄的身子更加黑瘦了,父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学校的老师也来到家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能这般不惜身体呢,累坏了将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老师的话,父母亲朋的关心,大家齐心协力硬是劝哥又回到了学校。 中学毕业,哥虽然学业优秀但考学无门不得不再回农村。他一回来便接替了招工出去的老会计的工作,大小也算个大队干部了。可毕竟不是哥的志向所在,在任上还没干到半年,到那一年冬季就开始征兵了,作为贫下中农儿子的哥很快就通过了体格检查和政审,从此,就离开家乡,在更加广阔的天地成就他的人生事业了! 3 “你哥最爱你了!”母亲常常当着家人的面对我说。 哥当兵出发的那天早晨,天还没亮,因他们一起入伍的人要带上大红花从公社统一出发,公社要组织敲锣打鼓,开欢送会。舍不下我的哥,硬是将还在炕上睡得正香的我从被窝拉出,穿了衣服,一直抱着我走到五里地外的公社驻地,我早已不记得哥在途中给我说了些啥,因为我当时也才4岁,而再次见到他已是三年以后的事了。队伍已经集合站队了,他才依依不舍的将我递到父亲的怀里。而母亲接到哥换下来的旧衣服包裹时也是手软的拿不住。 在那通讯落后的六十年代末,在三面环沟一面环山十分闭塞的铁炉塬,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通婚也仅限于方圆十里地,许许多多的人及至终老也没到过二十里开外的地方,而听到的更多的故事是,村上谁和谁那一年朝华山再也没有了音信;谁和谁在谋生路上遭遇了土匪一命呜呼;谁和谁出去讨饭客死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想当时是怎样一个悲壮的送别场面啊! 哥走了以后,母亲一个月都没有去洗他换下来的那一包裹衣服。她想着成天在一起撑持这个穷家的儿子,就这么一条线也没穿就走了,心里的滋味异常辛酸,她没有一丝力气去触碰那轻飘飘的破旧的衣物,虽然他儿子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是到外面的大天地闯荡,是开启幸福生活的前程,然而矛盾和纠结却这么撕扯着母亲的心。 哥爱打篮球,但每次都因为要照看年幼的我而不能上阵,虽然有时让别人临时替看,但总不放心,尽管如此,有一次大概是因为打篮球没有照看好我,让母亲打得几天不敢回家,只得在亲戚同学家借宿。哥走了后,母亲经常提起此事,充满了内疚和后悔。 小时候,我其实不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既不漂亮也很愚笨更谈不上好玩,我想,大概是从小成天看管着我,因而哥对我总是抬爱有加吧。我如今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他依然对我不怎么放心,每每打电话都时时刻刻的叮嘱我生活中要让着媳妇,不要太任性,开车要小心等等,这种小心翼翼的亲情似曾相识,这是母亲般唠叨式教诲,这种爱始终弥漫着我,让我不堪承重,常常使我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4 这次哥踏着春日暖阳,从人人向往的首都,从遥远的北京回来,我已经7岁了,我已经能提着小笼为自家的小猪挑草了。从此,有关哥的故事不再是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感受了。 在当时缺吃少穿的年代,尤其在农村,所有人的穿着除了灰色就是黑色,而且都是自制的粗布手工做成,穿在身上土不拉叽,粗劣异常。哥穿一身整洁的军装,面料比土布精细得多了去了,尤其闪光的帽徽和鲜红的领章分外惹眼,很让人羡慕。他整个人精神抖擞,干净利索,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粉丝围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里的小孩更是欢呼雀跃像糨子一样糊到跟前推脱不利,大人叫回家吃饭也不肯离开。在哥回家探亲的十天时间里,我寸步不离的跟随左右,除非他出远门。晚上他和父母家人或者亲朋拉家常,我也是常常瞌睡得上下眼皮合在一处睁不开了,也不愿睡觉。 哥回来后,免不了有村上的篮球爱好者相邀打球,每到这个时候,小伙伴们争相给哥拿衣服,而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披着哥的军装,头戴标准“雷锋”帽(我们也叫“火车头”帽),神气十足。常常有小伙伴央求想要戴一会,而我则根据自己对他们的好恶,分别给与他们时间长短不同的待遇。 想想这人性,在那么小的年龄竟能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无师自通的进行资源支配。可怜,可憎还是可爱呢? 哥是一个勤快的人,他见我的衣服脏了,就立即给我换洗,见我做事磨磨蹭蹭,就给我讲述部队集合队伍的故事,哥说,集合号一吹,几分钟内就要完成起床、内务整理、刷牙、洗脸等多项任务,见我不讲卫生,他还坚持每晚烧水给我擦身上的垢甲,洗脚剪指甲。 探亲时间很快就完了,哥又踏上了旅途,十多天里,小小的我着实为有这样的哥兴奋了一阵子,既感到自豪也感到骄傲,虽然没有上学,但生产队饲养室高墙上“全国学习解放军”几个大字我能读出来,因为哥是解放军,我家门上就有一块“革命军属”的牌子,很是显著,每到春节,学校的少先队员代表们还要在老师的带领下敲锣打鼓的来送春联呢,其时,母亲就会将自己做的我们最爱吃的柿饼分发给他们,那种自然流露的喜悦也会洋溢在母亲的脸上。 年春季,我上学了,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没有学前班,直接就上了小学一年级。上学后,哥送给我一枚红五星和一对红领章竟然派上了大用场。学校因为经常搞活动,排演节目给群众演出,像“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以及抓特务等有扮演解放军的节目,小学生爱演,同学们也喜欢看,而五角星和红领章紧缺,往往都是用红布手工裁剪而成,虽然耀眼,但却粗糙,哪能有我这货真价实的东西来得精致和夺目呢?于是大家争相来借,一时间这东西成了稀罕物,让我很是享受。遗憾的是,哥留下的“雷峰”帽,在呵护我大约四五个寒冬后,在一次看戏时,由于人太多,戏园子太拥挤,经历几次人潮涌动后给挤掉了,丢失了。为此,因为害怕母亲责骂,那天晚上我吓得迟迟不敢进家门。虽然母亲并没有太多责备,而在此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缓过神来,仍然闷闷不乐,不过他给我留下的那条军用棉大衣却陪伴我读完大学,一直到工作了以后好多年。 5 令人意外的是哥那次回来后只几个月又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居然没有穿军装。原来,哥要去上海复旦读大学,复员退伍了! 因为哥不再是令小伙伴敬仰的解放军战士了,“革命军属”的牌子也卸下来了,我心中不免有些小小的落寞。后来哥毕业后又被分回北京工作,之后就一直客居北京直到现在。 那时候,在村办小学上学的我,每到课间都要向老师们办公的土楼那边瞅一瞅,看看有没有那辆熟悉的,绿色邮政专用自行车停在那里。 公社送报送信的邮递员叫九娃,大约二十多岁,生得标致长得帅,穿着同样绿色的邮政专用制服,因为吃的是公家饭,穿的是公家的衣服,尤其是那种“邮政绿”在普遍是“穷汉”的庄户人眼里格外出色。他在方大圆大小群众中自然成了明星。 这九娃因为长年累月在乡下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穿梭骑行,练得一手好车技,他曾在学校操场表演大撒把精湛骑术,经常博得大家阵阵掌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tz/3911.html
- 上一篇文章: 头水香椿上市啦红河女子9元钱买了4小
- 下一篇文章: 石榴花开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