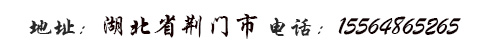对话努力呈现变革年代的历史纵深感关于
|
医院订阅哦! 年第22期·总第期· V S 对话 ← 李云峰 笔名云中君。运城文学院院长,《河东文学》主编,副编审职称;被选举为山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运城市文联副主席,运城市作协主席;文艺评论和文化散文为主攻方向,已有百余万字作品见诸文学报刊。出版有文化散文专著《石刻的历史》《访芮记胜》,即将出版文学传记作品《司空图传》。文艺评论曾多次得山西省文联文艺评论奖,并收录进相关获奖文集。年荣获-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 赵爱玲 → 笔名艾凌。山西闻喜人,现居河津,教师。热爱文学、心理学和太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评论、诗歌、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中篇小说选刊》《散文诗》《山西文学》《黄河》《都市》等文学期刊。获第六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留点空白留点想像》,著长篇校园心理小说《青春惑》等书。 爱玲的散文《我的土地我的家》,应该说是脱胎于她之前示我的《父亲的土地》与《庭院记忆》,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终于交融出这样一篇从土地的角度反映四十年农村变革的纪念之作,以一个离开土地的女儿的视角,关照自己的农民父亲匍匐在灵魂所系的土地上摸爬滚打、耕种收获的四十年。因为当初和作者的交流沟通当中,既记录了有关这一题材散文创作的意见,也包含了对作品理应具备的立意内涵的期许,所以,为了让其他写作者能更加真切地从中读出作者的创作构想与提升的脉络来路,决定把彼此间的创作对话整理呈现出来。 李云峰 爱玲好,稿子都读过了,谈点意见。 先说《父亲的土地》,以小见大,折射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由土地见证的巨大变化,立意没有问题,值得肯定。如果只读这一篇,有主要人物,有着重描写的土地耕种收割的变迁,有叙述者的真切体会与感慨,没明显的毛病了。但恰恰是《庭院记忆》,让我发现,前一篇所缺失的,就是具象的地域生活场景的模糊不清。也就是说,把老家的具体位置和居家的条件,包括地主的经济条件的前身,到最后无法长树的水泥铺设的庭院,都有机地融入其中,那么《父亲的土地》,会更具有历史的厚度,也就会更加对比出时代变迁的纵深感,其立意,似乎就不只是包含着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么一层浅显的意思了。我们老说要增加作品的厚度,具体到这篇作品的意见,应该是一次具体的践行机会。 回过头来再说两篇回忆老家庭院的同题散文,严格讲,都是程度不同的“庭院琐忆”,或长或短,都只是平铺直叙的片段罗列,或客观,或主观,皆缺乏一个核心主体的人物或者故事把它们有机地串成一篇完整的作品,现在真的只是形散无神的素材堆砌而已。 因为你是老作者,还兼顾评论写作,这样浅显的不足,应该知道,更不应该拿出来作为要发表的作品。又因为对你充满期待,又非常熟悉了解了,就不说客气话了,觉得应该坦率直言,才可能有激发惊醒的效果,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用意啊。 简而言之,如果把庭院和亲人的素材,有机而不是照搬地融入《父亲的土地》一篇当中,还可以调动其他我没有看到的生动素材,创作完成一篇优秀佳作出来,期待成为散文佳作! 赵爱玲 我诚恳接受李主席指点迷津,想写一篇有厚度的文章。 李云峰 谢谢你的理解,把意见作为参考,需要完全理解消化后,成为一种自然而然地去完成的创作。 赵爱玲 李主席,读了您的指导,我有点明白您希望有历史厚度,这对散文很重要。有个创作思路,想和您商榷。 从年以来,地主身份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范围。不过您看我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写及地主这个历史存在的产物:包产到户后,父亲开垦了很多小块地,但是地多了怕不怕政策改变?会不会因为地多再成为地主被斗争?在发生这个疑问时,加叙写出父亲作为地主前身因地多被斗争的往事。这也就写出了政府对待土地的态度的转变——解放初期,政府的土地政策一改旧中国土地是划分穷人与富人的根本标准,土地成为农村阶级划分的标准,地多被划分为剥削者为耻,成为被斗争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几十年不变的保障,土地又因此展现出空前的创造活力。另外,集体经济后又带出了为了经济发展毁林开荒,改革后也是鼓励开垦荒地,包含着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资源的畸形发展;后来沙尘暴,泥石流,暗示自然的惩罚,也促使政府调整政策,比如现在的退耕还林。父亲如今只耕种一块水地,其他的种了花椒树和核桃树,体现经济条件好了,温饱解决后,国家适时推出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政策。 李云峰 挺好啊,交织叙述,这就是纵深感的一种经营方式。地主的过往,与新中国土地政策的本质变迁,关系深刻,又能自然而然地触及到,多好。我已经想到了,相信其他有点年岁的读者,也一定可以有所联想与感慨。当然,如你所说,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感,必须认识到,这是不同社会制度实行的不同的土地资源所有制的革命性产物。 赵爱玲 如果写有追问的话,我想在最后写出,如今种了树木的土地上,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大都是老人;因为小麦等农作物买不上好价钱,无法养家,导致年轻人都选择出去打工,不少的土地撂荒了。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农村成了空心村。而父亲依然守在他的土地上,像一株老树深深地扎根泥土。 以我对土地的复杂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写出一个家庭一个人关于土地的纵横史,也通过土地经历过的阵痛,写出政府土地政策的变迁与一个家庭一个人的荣辱,写出国家宏大背景下的家族个人命运的沧桑。 李云峰 这些思考很到位,融入其中,夹叙夹议,自然会让作品的份量深沉厚重起来。好好改写完成吧,一定会有效果的! 赵爱玲 最好题目换个新的? 李云峰 目前的感觉,这个还可以,让我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但你笔下的父亲,有所推进,赋予了新的内容。这是我读这篇散文时,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赵爱玲 我得看看那幅油画。 李云峰 这幅油画作品只体现出改革以前的农民忍辱负重般的沧桑感,而你,则应该写出进入新时代的万千农民“父亲”所应该具有的情感、思想、精神层面的典型蕴涵。 赵爱玲 好的,我努力把这篇父亲的土地史诗写好。 李云峰 期待着! 就作者现在的完成稿而言,以上探讨的内容,有些得到了适当的充实体现,并有新的拓展,也有一些回溯与思考的层面,还显得有些薄弱。但是总体而言,通过父亲所伺弄的土地,读者不但可以感知到这位千万农民“父亲”的代表者所经历过的观念转变的心路历程,更可以深切感知到发生在农村土地上的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和农耕文明面临崭新嬗变的进步履痕,这样的立意与表达,值得肯定。 另外,作者通过对作品新确定的题目《我的土地我的家》的说明文字,其实就是对这篇散文立意的诠释,颇见作者理性思辨的功力,故照录如下: 因为贯穿全文的情感线索是我对土地的复杂的情感变化,所以“我的土地”,既包含我生存的物质的土地,也包含我耕耘的精神上的教育沃土;“我的家”既代表我们这个家族的小家,也反映“国家”这个大家。文章以父亲带领我们全家人在土地上的劳作故事为纵线,我们的具体家庭生活为横线,通过父亲和“我”对待土地的不同情感推进,架构起纵横交错的立体化的叙事。以“我的家”的沧桑变化,以小见大折射出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适应特定发展国情的土地政策,反映改革开放下的农村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文明与进步,从一个家庭看农村的变化,国家的发展,民族精神的传承。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旨。 作品赏读 我的土地我的家 赵爱玲 1 我的家在太行山支脉焦山脚下龙王泉畔,门前小桥流水。那水是从龙王泉里流淌的正宗的泉水。印象里,我放学回来,老奶奶盘腿坐在门前的小桥上,做着针线活儿。我会在老奶奶的怀里撒撒娇,然后蹲在小河边玩水…… 我家紧邻河水,是一座前后四合院。前院西厦檐下,有一棵树冠直径约三米多的石榴树。五月,火红的石榴花开了,像一个个小喇叭,花瓣中间星星点点的淡黄色的花蕊在微风中抖动,一片片椭圆形的绿叶点缀着一簇簇红色的石榴花,树影婆娑,院子里溢满芳香,引来蝴蝶和蜜蜂。儿时的我搬个小凳子,背靠着树干,读爷爷的书姑姑的书父亲的书。 我对石榴花情有独钟,倒不是因为石榴花有多好看,而是当年同学们中流行一种手抄本,类似如今星座之类的生日预言。说在石榴花开的五月出生的人爱好文艺,努力坚持可能会成为文学家。那时候,七八岁光景,对于文艺、文学之类的词语也并不清楚。后来随着对书籍的痴迷,渐渐明白了一点,对石榴花也就有了特别的情愫,更加悉心地给它浇水,还给它念书听,尽管我懂得那种预言并不可信,文学对于我,也仅是生活工作之余滋养心灵的兴趣爱好而已。这棵石榴树,在30年前,我老奶奶去世那天被砍掉了。它和老奶奶一起活在了我的记忆里。爷爷生前有个愿望,希望写出自他父辈以来家族的记忆。后来,我爱上文学,也发表了一些文字,爷爷未完成的愿望成了我的愿望。我想写一写我生活的土地,我的家。 我家四世同堂。老奶奶,爷爷和奶奶,爸妈,我们姊妹六个,全家11口人,一口锅里吃饭,这是我们村里最大的家庭。我和三妹跟随老奶奶住,二妹随爷爷奶奶住,其余的妹妹跟爸妈住。 那时候,父亲的钟声就是我每天上学的闹铃声。 父亲是生产队队长。每天早上6点他就敲响了村子中央的铁钟,“铛——铛”,社员们就提着农具到钟下集合,听父亲分工。老奶奶一遍遍地喊我:“玲啊,玲,起来,上学啦!”我每天晚上要纺一个线疙瘩,然后就着油灯写完作业方可睡觉。所以,早上老奶奶一叫我,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是迷糊的,眼皮也睁不开。直到天儿大亮了,我才在老奶奶反反复复的喊声中急慌慌地爬起来。背着书包一溜小跑,远远看到学生正在操场里跑操,校长站在边上巡查。得想办法趁校长不留意插进队伍,不然要被罚的。我站在操场北边的破墙根,身体隐在墙后,一只眼睛对着墙缝,心里扑腾腾地跳着。这时候就有三三两两的小伙子大姑娘扛着锄头或者铁锨嘟囔着:绝后的××,这么早,又要扣工分了……我分明听见他们是在骂我父亲。我又气又羞,心里埋怨父亲,干活又不是上课,今个完不了不会明个吗,干嘛非催着人家早起?再说了,睡不够多难受。我正探头探脑,冷不丁就被校长发现了,我耷拉着脑袋,满面羞惭地背着书包从村南头到村北头,来回跑三遍……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一路上,总会遇到大姑娘小伙子埋怨父亲的牢骚声,更有过分的还朝我吐唾沫。 隔三岔五就有小伙子或者大姑娘站在我家门前骂:“绝后的××,我吃队里的,吃你家啦?你他娘的少管……”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撞见我家邻居的姑娘小芳耍泼,她滚在我家门前连骂带哭:“我锄坏了玉米,我就故意咋啦?又不是你家的,你罚我返工,还扣我工分,你活该绝后!”她看见我就冲着我骂,“活该!” 老奶奶在屋里捂着脸抹眼泪。我惊恐地望着她,她用大黑襟裹住我,抱着我说:“没事,你爸没错,他就是太过认真了。唉,可都不认真吃啥啊……” 那时候,我有四个妹妹了。 我隐约明白了一些事理。 看见社员上下工,我自觉地回避到一边,或者埋下头快步跑过。 不知道父亲是否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我不止一次地在老奶奶面前哭诉。 我对于土地的恨意,就在那些骂声之中,一点点地滋长了。 2 土地包产到户以后,父亲再也不用敲钟了,也再不挨骂了。大家见了父亲都很尊敬,经常请他去地里指点,比如怎么给棉花择叶,怎么种红薯保墒,如何给种玉米授粉……那时候,我走过人群时,再也没听到埋怨父亲的声音,不仅如此,我还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流露的敬意…… 老奶奶说,不一样啊,以前给生产队干,你爸爸遭人恨,现在给自个干,你爸爸是香饽饽啦!谁见谁敬着呢。 老奶奶看着美滋滋的我,揩着我的鼻子说,看把你乐的,你爸爸是个好庄家把式!庄稼人就认这个! 我家人口多,分得土地也最多。可是我们家没劳力,就我爷爷和我父母三个人。于是我们就成了小劳力。 每年春季,一到星期天,父亲5点多就把我们从热被窝里喊出来。我们扛着锄头,提着绳子和镰刀,背着干粮袋子和水壶出发了。我家的地在中条山顶,大约15里路程,从山底到山顶,坡很陡,到不了半山腰我们就累得走不动了。赶到山顶,太阳已经老高了,父亲已经锄了一小块地了。父亲手把手教我们锄地,他先让我们分清麦苗和杂草,然后示范,前腿要弓,后退要前伸,手往后拉。他过一会返回来检查下,看我只除草,就说,我们是锄地,没草的地方要松土。因为父亲反反复复地检查,我们不断地返工重做,我们的活儿也就越做越慢。眼看和父母的距离落得越来越远,我们也就失去了干活的心劲,干脆坐在地头玩起了蚱蜢。用马尾巴草茎从蚱蜢脖颈处穿过,打个结,两两相斗……父亲正要吆喝我们,就听见妈妈高声地吵父亲:“你当孩子是你的社员啊,差不多就行了!都停下,到埝头柿树底下吃馍!” “噢,吃馍啦!”我们把手在衣服上搓几下,一人一个馍馍,馍馍是大部分玉米面和一小点白面做的,这比以前的玉米糕好咽多啦。一口馍,一口大葱,好吃极了。父亲三两口吃完了,就兀自蹲在地里捡拾刚才锄的草,码成捆放到地脚头,回家的时候背回去喂牲口,我们家十几亩地全凭牲口拉犁播种,牲口圈里养着一头驴子,一头犍牛,还有一头小母牛。三头牲口每天要吃很多草,堆起来小山一样高吧! 等我们吃完了馍,父亲就吆喝我们开始干活,山顶上我们家有五块地,父亲分给我们一块,说干不完不许回家! 春天的太阳虽然不毒,可是一天下来,我们又累又渴,感觉夏天般炎热。干干停停,就这样一直干到下午。父亲干完活儿,让母亲帮我们,他自己却下到山坳里垦荒地,他垦出很多小块地,有的只有两三平方米,有的地块稍大点,这样的小块地加起来比人口少的家庭分的土地还多。这是又要当地主吗?我实在害怕填写家庭成分。我害怕听到同学们喊我“地主家娃”。 白天干完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完作业,老奶奶安排我做活儿,她纺棉花,我缠穗子。一边干着活儿,老奶奶一边讲我家的历史。 老奶奶17岁嫁进门时,老爷爷已经29岁了,因为家寒,老爷爷娶不起媳妇,只好娶了没有父母的我的大脚老奶奶。在那个崇尚好女三寸金莲的时代,老奶奶长着一双没有缠过足的大脚,嫁到我家很长时间都会遭到乡人明里暗里的讥讽。老奶奶说:“命薄像张纸,勤劳饿不死”。在老奶奶勤俭持家下,解放前夕,我们家已经成为当地的大地主,村里人按照方位尊称我们家“东院”(由于院子里有棵树龄近百年的老榆树,我家也被称为“榆树院”);另外一家地主被称为“西院”。在爷爷五六岁时,老奶奶给爷爷专门请了先生接受教育。爷爷好学,后来成为精通四书五经,天文地理,易经八卦,数理珠算,赋诗作对的乡村德高望重之人。在斗地主的年月里,由于老奶奶平日乐善好施,也因为她时刻教育家人遇事宽厚、谨言慎行,爷爷以厚德学识服务乡邻,一家人忍辱负重相依为命度过艰难岁月。 父亲没完没了地垦荒,让我敏感的心里充满忧虑。但是,父亲却乐此不疲,一座荒山在我们一家人的汗水里,变成了一块块梯田。 这样的小块地因为地势偏狭,无法使用牲口,就必须完全靠人力,犁地播种都由爷爷整靶,父母和我们用绳索拉,我们就像列宾油画里的纤夫。父亲在小块地里种上蓖麻、豆子、红薯等一些耐旱又好生长的农作物。秋收以后,全都种上小麦。大部分山里人,因为土地多,又因为贫瘠,只种一料麦子,可是父亲总会在差不多的土地里,种两料作物,这加重了我们一家人的劳作,每天腰酸腿痛,没有闲过。 每当读到“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我会感同身受。在儿时的意识里,土地上的劳作即苦难,它深深烙在我的心里。 劳作之余,在高山之上,我会无数次想像自己能够长出一双翅膀,飞离土地。 3 前后院之间的三间北房是我家最新的房子也是地基最高的大瓦房,正对着大门,是院子里最气派的房子,但是从来没住过人,房子里供奉着我的祖先们。房子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正中是一张八仙桌,摆放着我祖先们的相片,正中的墙壁上是祭祖的大幅挂图,两边是一副对联:“慎终须近三年孝,追远常怀一片心”。每逢过节,我们都会在饭前把最好的菜肴端到这里,摆上四个碗碟,四双筷子,点上香火,低头跪拜祖先之后,方可吃饭。这个房子一直保留到年我们家拆旧宅盖楼房为止。 我爷爷是独子,也是有名的孝子,老奶奶给他起名叫善和,后来爷爷给我爸爸起名叫忠孝。爷爷常常给我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他说年轻时(战乱)他受聘到外地当官,他以自己是独子,长子不远游推辞了,然后隐居焦山做了数年私塾先生。我记事起目睹爷爷每天早晚到炕前问候老奶奶。特别是晚上,爷爷是大队会计,不论回来有多晚,他都会坐在老奶奶的炕头,说世情聊家常,直到看着老奶奶睡下了,为她盖好被子,方才离开。 四合院,留下了我家祖孙四代多少温暖的记忆。 门楼下有个土坯垒的三角灶台,得空的时候母亲就往灶火里塞几把柴火,烙煎饼炒豆子。爷爷和我们爱吃马齿苋煎饼。每年春天,是马齿苋狂长的季节,小河边,田地里到处都是鲜嫩翠绿的马齿苋。我们摘了嫩叶,奶奶洗干净,母亲把菜叶切碎,倒在面盆里,加适量的面粉,放点调料和盐巴,不断搅合,直到菜与面粉混合成面汁。我们常常围在灶火边,等着煎饼出炉,只见母亲用绑着干净碎布条的筷子,蘸点油,在锅底来回抹,然后舀一勺面汁,在锅上面一边悬一边倒面汁,“磁啦”一声,母亲双手捏着锅耳朵,弯腰来回一高一低一左一右地旋转,我们的目光也随着母亲的手,一高一低地转动着,面汁均匀地覆盖在锅底,锅底随着“吱吱”的干裂声,形成一个薄薄的面饼。她操起小铁铲,面饼翻一个身,顷刻间,香气扑鼻而来,很快白绿相间的煎饼就要出锅了……我们会把第一个煎饼端给爷爷吃。我们一边剥蒜捣蒜,一边继续等着煎饼出锅。煎饼蘸蒜泥是祖先流传给我们的吃法,也是在我们看来最香的吃法。浓浓的马齿苋煎饼的味道,浓浓的蒜泥香味,还有一缕缕的炊烟的味道……我们一边吃一边赶着闻香而来的母鸡公鸡们,爷爷会笑着扯下一块煎饼让鸡们吃…… 从前院到后院要经过一条长四五米的狭窄的甬道。甬道东侧是父亲的铁匠铺。父亲十三岁学艺,后来成为当地有名的铁匠。遇到雨雪天气,不能下地干活,他就在阴暗的铁匠铺打造各种农具和建筑用的铁钉。爷爷轮大铁锤助力,父亲轮小铁锤塑型,我和妹妹们一边写作业一边轮流给父亲拉风箱。在这个不到5平米的小铺子里,冬天还好,夏天就闷热难忍了。没有形状的厚铁块,在炉火中煅烧,然后父亲用钳子夹出闪着火花淌着铁水的红铁,“磁啦”一声,放入水中淬火,接着左手使钳,将铁片置于铁砧,翻转,右手用锤,“叮叮铛——叮叮铛……”有规律地反复锤打……废铁由厚到薄再到成型,千锤百炼打磨成精致物件。炙热的气温和炽烈的炉火,使父亲汗流不止,浸湿地面……父亲被飞溅的铁水烫伤是经常的事情,而他像抹去灰尘一样擦掉铁水继续干活。有一次,伤了眼皮,幸好没有伤到眼珠,但是眼部肿得像馒头……由于父亲的手艺精湛,名扬方圆数里,定货不断,活期又紧,所以父亲往往昼夜不息…… 在乡村,冬季是一年中的休闲时光。我们一家却在陪伴父亲打铁的日子里度过。生活的艰辛,一家人围在炼铁炉边奋斗的温馨和力量,使我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将来不再让爷爷和父母过劳碌的生活。我虽柔弱,但做事坚持如铁,这多源于儿时的历练。 每年农历五月初,我们的村子最忙碌。由于麦子和大蒜是同期收获,所以我们夏收的劳动量是双倍的。那时候家乡还没收割机,完全是手割。与此同时,水地的大蒜也到了收获时节,错过了收期,大蒜头一旦脱茎,就没法编成蒜辫子了,也就卖不成好价钱了。大蒜的收成是我们家吃穿用度的主要来源。 每天早上四点多,父亲就叫醒我们,父亲背着一捆镰刀,赶着我们上山。天上还有月亮和稀疏的星星,困得几乎睁不开眼睛,我们一路走一路看星星,不看星星,我们会打瞌睡。父亲说,起个早,天凉快,等太阳出来了,咱就干完了…… 可是会吗?那么多的土地!我的手上满是血泡,老痂还没脱落新伤口又出现了,手指伸不直,腰痛腿酸,一坐下就不想再起来了。任凭父亲怎么说怎么吆喝,我也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蹲坐在地头,晒得头发晕,我抹着眼泪在心里发誓:“我要离开这里。”那时候,我是那么憎恨土地,那么憎恨土地里没完没了的劳作。 我无数次下决心好好读书,永远离开土地。很多年后的一天,我读到鲁迅的句子:我们热爱故乡的文化,却并不热爱故乡的土地。难道不是吗?我们在血液里爱着故乡,却一个个拼命远离故乡,而离开的理由就是土地。 然而,我的父亲,他是那么痴迷在土地里。他一边收割,一边快乐地甩着汗瓣,他不说话,可是笑容在他的眼睛里。当他把麦捆扛到木制平车上,又返回地里捡拾一根根麦穗,像在怀抱一个个孩子…… 晚上,我们都累得睡下了,父亲却撂下碗筷,去了水地收大蒜。那些大蒜深埋在泥土里,要手握蒜刀一个一个地挖出来。母亲躺一会也出去收蒜去了,我负责照看妹妹们睡觉,看家。 遇到雨天,劳累的人们也该歇息了,可是我们村的人们更忙了,那些因为收割麦子堆积如山的大蒜,蒜叶已经发出腐烂的气味,再烂下去就无法编蒜辫子了。家家大人小孩齐上阵。父亲教会我,我教会妹妹们。 白天,晚上,直到编完,直到雨停。我们满手黑绿的污泥,浑身上下弥散着腐烂的蒜臭味…… 天晴了,我们跟着父亲继续收割麦子。我们把麦子摊在打麦场,父亲吆喝着我家的两头牲口,拉着石碾子碾麦子,我和妹妹拿着铁锨,等父亲喊:“接屎!”就急忙小跑着赶过去,把铁锨放在牛屁股下……后来,碾场就用上了四轮车,我不用再跟着牲口满场跑了…… 碾完了麦子接下来是晒麦子,拣个太阳好的日子,父亲头戴多年的破草帽,衔着一根烟袋锅子,把一袋袋麦子用小平车拉到场院里,摊开,然后脱掉鞋子,光脚在麦子里犁出均匀的麦沟,像这样一天要反复几次,我试过一次,脚丫子烫得我直喊叫。别人家嫌麻烦,只晒一次就归仓了,父亲却总是拉进、拉出反复三次。他说功夫没白费的,彻底晒干,不生虫子不发霉。 晒好的麦子被父亲一袋袋倒进他亲手做的砖粮仓里,透气但不漏洞,老鼠进不去,就连虫子也只是在仓外徘徊…… 夏收和秋播之间的日子是农闲的。没有那么忙碌了,父亲还是起早贪黑,早上我醒来时,父亲已经割草回来了。他说这个时期,人休息,也是牲口静养的时候,必须让牲口吃饱吃好,到了秋播时机,牲口才有精神干活。平时没事他就储存农家肥,把牲口圈里的粪土一车一车铲出来,堆积在水地头,然后浇上大粪,开始蓄粪。我们家的庄稼长势好,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父亲做农活细致认真,一个是父亲舍得施农家肥。一般人下不了那样的苦,所以地里不是杂草高过庄稼就是庄稼叶子色泽浅淡,打卷,生虫子。 每当我和父亲经过庄稼地时,父亲总习惯评点一块块庄稼。当路过庄稼矮小,杂草疯长的地块时,他总会惋惜地说,看看,庄稼做成啥了! 那时候,我总会听见人们经过我家土地时说:这家的庄稼做得好啊!听到那些关于父亲的赞誉,我由衷地开心,也觉得自豪。 父亲用了他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垦荒种粮,我家成为全县有名的种粮大户。父亲被评为县级模范,政府还奖励了我们家一台拖拉机。在锣鼓声中,父亲披红戴花,被乡邻们稀罕地簇拥着。 我们一家人,坐着拖拉机收获庄稼,在村民们的注目礼中,风从耳边呼呼地刮过,作为大地的主人,我感觉无上荣光。 我明白,所有这些都是土地给予的。对于土地,我充满复杂的感情,既恨又敬畏。 4 我家后院西边是牲口的住所。一般情况,这里的食槽里喂两头牲口,有老牛和小牛。还曾经喂过一头毛驴。毛驴和小牛搭配着使用,老牛单独使用,这样可以使牲口们轮流使唤,不至于累着。 暑假是城里孩子的天堂,可是对于农村的孩子,尤其是我们这样有着很多贫瘠土地的山村孩子,暑假是炼狱。大部分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割草。那时候,各家都养着一两头牲口,对于农民来说,牲口几乎是家中一员,它是家庭的主要劳力,而草是牲口的口粮,割草对每个家庭来说,是大事正事。经常吃青草的牲口膘肥体重,经常吃干草(麦秆)的牲口松垮瘦弱,看每家的牲口,也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是勤劳还是懒惰。那家的女儿或者儿子天不亮就背着满满一筐青草回来了,那女儿或者儿子的勤劳的好名声就出去了,而且十里八乡地远扬,提亲的说媒的踏破了门槛…… 每天割回来的草,堆得像座小山。傍晚,父亲叫我和他铡草,就是那种貌似古代刑罚里的大铡刀。我双手使劲按着铡刀,父亲单膝跪着用双手入草。我偶尔听说某某的手被铡刀铡掉了的事情,所以每次按下铡刀时我都分外小心。铡完草我总会小心地舒口气,感觉自己像个刽子手。 别人家的孩子只是早上割筐青草,就可以玩一天了,我的父亲还要带着我们天天到旱地杀埝。用我现在的理解,杀埝的原理就好像给土地做个全方位的美容。先用斧头或者锄头把埝墙上的荆棘、杂草清理掉,这就好像给人洗脸去污,然后用锄头刮去埝墙的表皮,这好像给人去死皮敷面膜。据说埝墙上刮下的土是上好的肥料,能够滋养土地,所以最后一道杀埝的工序才是最重要的,用铁锨把这些埝土均匀地撒在土地上……像这样做土地,在我们村也只有两个人,村西头的老夏头和我父亲。老夏头已经去世了,只有我父亲还这样做土地。他做土地就像在养人,过上一两年,他说这块地需要休息,只种点秋作物,不种小麦了,缓缓气。大家几乎不这样做了。很多人已经把远在中条山上的土地撂荒了,因为这些土地由于从来没施过肥料,再加上只靠老天下雨,一亩地打不下多少粮食。 上世纪90年代初,仿佛是一夜之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男人大都去了工地,女人大都到饭店洗碗……土地大片撂荒了,杂草丛生,完全没了土地的样子,父亲看着,叹着气,土地全凭人做啊……他感叹,农民抛掉了土地,就忘了本,那还是农民吗? 大片土地荒芜的同时,人们开始靠山吃山。随着一座座石灰厂、石子厂的崛起,焦山这座石头山开始热闹了,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人肆意开凿,点炮,打眼,一车车石头运往山外,焦山像一个孤独的被遗弃的老人一样,千疮百孔。 中条山的风越来越大,风沙漫漫,泥石流频繁发生,在一次泥石流过后,几家山里人的房子倒掉了,幸好人没事。山脚下的村民开始逃离。村子一点点成为空心村。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故乡在一座名为“焦山”的山口叫峪口 山上少土而多石头 贫瘠的土地上长满沙棘 拼命向外生长 成为每个孩子成长的动力 故乡不断向外迁移与输出: 升学、出嫁或者入赘他乡 攒足了钱到城里买房子 一块块巨石不断被运出 焦山,一点一点荒芜 焦山,一点一点矮下去 我和我的姊妹们一个个憋足了劲儿都发愤读书,想要离开土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贫瘠的土地上有限的收入逐渐吃紧。我上大学二年级那年,听妈妈在信里说父亲随着一个建筑队在我所在的城市打工!那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父亲也终于不得不远离家乡……多方打听,我终于在一个小工地上找到了正在施砖的父亲。 在高高的墙上,父亲一手抹着水泥,一手小心翼翼地堆砌着砖块……秋天的天空格外高,格外蓝,羽毛一样的白云在父亲的身边漂浮着,流动着。在城市,在异乡,我仰望着父亲,不敢大声叫唤,我担心蹲在高墙之上的父亲分心。我久久地望着,望着……亲切和难过交织的感觉使我想哭。 这一年,父亲没杀埝。他一直辗转于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 5 后来,我的三妹、五妹、六妹等相继考上学校,那时,大学并轨了,学费相比以前高多了。我已经在外成家,我卖掉自己还没来得及装修的房子,和父亲一起供妹妹上学。父亲来往于土地和工地之间,二妹已经招了上门女婿(家乡称弟弟)。弟弟要和父亲一起供妹妹上学,可是父亲谢绝了,父亲要凭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女儿养大成人。 与其他农民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父亲首先种好土地,然后才去打工挣钱。旱地是粮仓,水地是庄户人家的钱袋子。父亲把所有的水地都轮种了大蒜和玉米。寒冷的冬天,庄户人大都坐在炕头暖和、打牌、闲聊,父亲用自行车载着大蒜走街串巷叫卖:“卖蒜啦,峪口白玉蒜啦!”早上5点多就出发了,晚上11点多才回来。母亲和我们经常站在村头等啊等…… 就这样,父亲靠着土地和打工,供我们姊妹几个毕了业。我们在外结婚成家了,希望父亲可以放松了。我们劝他把土地交给弟弟,到几个女儿家轮着住,安度晚年。 这几年,我们几个都在各自的城市买了房子,还清了房款,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三妹带父母在她武汉的新家住了三个月,陪着父母在武汉长江大桥散步,坐轮船,逛公园,六妹带着父母游北京逛西安。弟弟拆掉了家里的旧房子,建了五间两层小洋楼,三个孙子健康聪明,父母过着平静幸福的晚年。但是,父亲不论在哪个女儿家,只要估摸着到了农忙时节,他就立马要回家。他时刻惦记着他的土地。 记得有一天,我在电话里劝父亲别到地里拼命干活了,我们做子女的只希望父母健康平安幸福。父亲在电话里说,咱们家的旱地只留下一块离家近的种了麦子,其余的都不种了,国家施行退耕还林了,咱家种了核桃树和花椒树。父亲开心地说,那块种麦子的旱地,平展,不用人力了,播种收割都用联合机器,直接就把麦粒送到家啦!国家现在政策好,取消了农业税,种树还补贴粮食,这可是从来没有的啊,种小麦玉米国家还补贴钱,…… 听他的口气,好像是还要在土地上大干一番的样子,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父亲和母亲都有心脏病,我希望他们的晚年能够离开土地在城市安度。我们有这个能力。自从父亲做了肾结石手术,特别是突患心梗停止脉动紧急抢救之后,我反复劝他,你要服老,不要拼命干活了,现在的生活好了,粮食充足,钱也够花,您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您应该享福了,我们做女儿的都有养老的义务,您也让我们尽尽义务。 就在我们计划着说服父母离开土地时,一向健壮的弟弟(二妹的丈夫)突然离开了人世。父母和二妹还有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三个幼小的孩子忽然之间失去了他们最爱的爸爸,父母失去了孝顺的儿子,二妹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丈夫,而我永远失去了敦厚善良的弟弟……我故乡的家,顷刻之间失去了顶梁柱……从未在我们面前流过眼泪的父亲,放声痛哭。年迈的双亲几乎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发,苍老下去。 我们抱头痛哭。父亲放声痛哭之后,再也没有流泪,他叮嘱我们不要在二妹跟前哭。 我年近花甲的父亲再次成为我们家的精神象征,他用他的行动劝说母亲和二妹面对现实,三个孩子还小,生活还得过下去。他又像壮年一样,全身心扑在了他的土地上。他更加细致地给土地做着美容,他把土坷垃碎成柔软无比的丝绸……他把蛐蛐带回家里,用麦秆做成精致的房子,他在花池里种下的南瓜和丝瓜,爬上了二层楼的围栏……我三岁丧母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从小练就了化解悲伤的功力。普通的柳条在他手里会被编织成精巧的篮子、背篓;原本同样贫瘠的土地,一经他的双手,就变得肥沃,打出双倍的粮食…… 我年迈的父亲,学会了打牌、下棋,他不再拼命地干活,他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不能倒下。他轻松自如地做着他的土地。他仿佛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他自由自在地规划着土地,蒜地里套种玉米,玉米地里套种豆子,地垄上种辣椒……他把平面的土地做成了充满立体感的艺术。 一想到土地上忙碌的我的父亲,我很难过。我是那么想把我的父亲从土地上带到城市,从此离开劳作,过我认为安逸的生活。 6 一家人的勤劳和善良也许感动了上苍,一位善良的弟弟走进家门,对三个年幼的侄儿侄女视若亲生。转眼间10年过去了,如今弟弟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大女儿还读了重点大学的博士,二妹和弟弟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大学,外出打工,父亲和母亲守在家乡的土地上。 去年春节姊妹们回家,劝说年事已高的父母,把土地全部承包给他人,可是父亲坚持要留下一小块水地和几亩旱地。他说如今也不用咱的人力了,打个电话就有人开着机器来,让我们不要操心家里。父亲说,你们放心,现在村民看病有医保,每年还有免费体检,我们这些60岁的老人,国家很照顾,每年还有免费旅游…… 土地里的活儿少了,父亲就到山上给人做护林的活,除草,种树,剪树枝,浇水。每天按时上下班。 我们姊妹每月定期给父母打生活费,给父母置了老年代步车,早上,母亲坐着父亲开的代步车到早市喝豆腐脑,买新鲜的蔬菜。傍晚,母亲和邻居相伴绕着村子散步、锻炼。 如今,村里早已没了牲口的踪影,也再没有背着筐子割草的孩子的身影了。机器早已经把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村民们过着城市一般的生活,洗澡,看电视,旅游,上网……人们不再起早贪黑,他们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每次看到沧桑的父亲,曾经因劳累和悲伤浇铸的花白的头发,因经常暴晒的黝黑的面容,青筋暴露的粗糙的手,我的心依然会痛。 每逢冬天,我都会劝说父亲和母亲来城里过冬,父亲总是说,家里也烧着暖气,不冷。 我多么希望,我劳碌一生的父亲和母亲能够在晚年离开土地,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城市。当希望一次次成为奢望时,我开始反思自己,我的父亲在城市里生活的日子真的快乐吗?他因为用不惯座便器每天早上宁肯到公园找公共厕所;他因为不习惯没事做,每天把家里的地板擦了又擦…… 我常常问自己,你爱这块土地吗?实际上,我在外游离的日子多于在家乡的日子,回到家乡,看到的多是陌生的脸孔。住不了几天,我就会因为工作着急回城里。 也许,土地里的父亲才是快乐的自在的。正如我站在讲台上是快乐的,痴迷文字是自在的。孝顺并不是非得带父母离开土地。此时此刻,我甚至认为,土地并不是具象的泥土的组合,它更是抽象的精神集合。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吧。 每当迎来一批新生,我如农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耕耘。每当送走一批学生,我像父亲站在丰收的庄稼地一样,挥着汗水,满心喜悦。 原来,我也一直行走在我的土地上,这是我的精神家园。 慢慢的,面对家乡和土地,我的心里多了一份释然,同时对田园生活充满了向往。在夫家的小山村,我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春夏凌霄花爬满枝头,秋季菊花开满院,冬季腊梅花绽放……每到周末,我给自己断网,回到这个“世外桃源”,不看 如今,我故乡的农田已经变成了绿树环绕的樱桃采摘园、葡萄园、核桃园、花椒园、椿树园…… 曾经,我无数次梦想着逃离的土地,已经成为我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老奶奶、爷爷、奶奶已长眠在那块土地,我也人到中年,姊妹六个天南地北,远离故土。家乡的小河依然流淌着,两边的院子里看不到垒着烟囱的泥瓦房了,都是整齐的楼房。庭院里也大都是水泥地板,没了树生长的地儿,没了牛马,也没了公鸡母鸡的影子。 伴随着成长与发展,我们也在经历着丧失。 我的土地,我的家,还有火红火红的石榴花,香气扑鼻的马齿苋煎饼……在梦里,在我的心里…… 编辑 悦 芳郭萍萍 图片 作 者网 络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liuhuae.com/slhtz/5213.html
- 上一篇文章: 生命在生活中进行,无止,无尽和你读诗第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