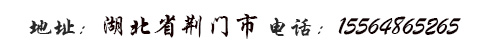河南作家王朝君仙妻如烟
|
■■ 心情音乐 边听边读 仙妻如烟作者:王朝君 木根卖过西瓜便凝视这座陌生的城市。 木根来过这座城市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以至于他对这里梦一样的陌生,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经踏过这片土地。 木根想,到底这次来是卖瓜还是寻妻,也许卖瓜是个理由,也许寻妻更是个借口,偌大的城市他真的能寻到妻吗? 妻这个在他脑海里早已淡化的概念,刚一浮出时,还有些激动不已。然而,当他卖过瓜,眼看着陌生的街道、陌生的车辆、陌生的行人时,一切寻找的欲念,瞬间便化为乌有。木根忽然又想起了他的瓜棚,想起他瓜棚里早熟的西瓜,想起了卖的好行情。早春天冷,许多瓜苗都冻死了,只有木根护得好。木根吃住在瓜棚里,西瓜苗是他一个个的孩子,他每时每刻都精心地照料着,照料着他的儿女分蘖、拖秧、开花、结果。 “木根呀,你把瓜伺候得那样好,让我们回家挨老婆的气呀? “木根呀,你整天爬到瓜棚里,别也成了瓜。 “木根呀,你干脆将瓜做了你的女人吧。” 瓜棚是木根的家,瓜苗是木根的儿女,瓜身是木根的女人。木根忽然想起了家,想起了以往的家,想起了现在的家,想起了熟悉而陌生的家。以往的家是三间西屋,陡子砖瓦屋顶,墙根的老砖已少半风化为砖面,他小时候就用手剥那老墙土,让飞虫在手边飞来飞去。木根后来就死了爹娘,孤儿的木根,在二叔的照料下偷长成人。“这孩子真是白拣了条命。”木根现在见了村里的老人时还时而听起。木根想能活命就算不错了,所以就没往深处想。木根是在遇见伊莲时才忽然有了想要女人的念头。伊莲是位貌若天仙的姑娘,木根这样想了,村里人也都这样想了。伊莲十几岁才回到这个村子,村里人仿佛谁也说不准伊莲的亲爹。个别人记得,有一个东北来销干货的老板,长得高个子,白镜子,大眼睛,惹得大闺女小媳妇现在闭上眼睛都能想起他的模样。卖干货的男人住在村西头的二香家,二香家的北墙外就是寨墙。--有空闲,二香就陪那男人,翻过寨墙,来到柳树下,来到小河边,他们说呀、笑呀,不顾間围躲藏着的小子们窥视。男人就让二香帮着他卖干货,二香来到哪家,哪家的女人就说让东北的客当面谈吧。女人们喜欢东北人的口音,更喜欢看一看这个村寨里少有的潇酒男人。男人就笑着将女人的钱兜满腰包,腰包鼓囊着的男人就悄无声息地走了。男人走后的一些日子,二香的男人刘长忽然到邻家找二香:“见二香了吗?”“见二香了吗?”刘长挨家挨户地找,刘长一天一天地找,直把日头找黑,将黑夜找亮,终于没找到二香。刘长就一天一天地领着儿子刘杰在村西头等,村东头等,村南头等,村北头等。 “别等了,二香肯定跟那个东北人跑了。” “别看你得了人家的好处,可如今老婆也搭上了吧?” 刘长没有唤起村寨人的同情,无奈刘长只好携儿子刘杰奔波东北 想不到三十年过后,又一个男人在城里寻找二香的女儿。 “二香回来了,二香回来了。”再没有比这个新闻让全村人沸腾了。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几乎是每户人家都倾家出动,将刘长家堵个水泄不通。人群一批一批地去,一批一批地回,一-批一批地啧喷称赞,一批一批地惊叹不已。直到快到黄昏时,木根才胆怯地过去。“这是谁家的孩子? 一个烫着发卷又皙白的妇人指着木根问刘长。木根想这可能就是二香了,一副城里人的装扮。 “这是怪手哥家的木根,你不记得了吗?那个大拇指上又多一个小指的怪手哥。 ‘噢,我想起来了,在队里时,他看场,总是捧给我们烤好的花生。我还扳过他的怪指呢,把他的脸都扳红了。” “可惜他早没了,一个好人。你走后没几年,先是木根他娘得癌症死了,过两年怪手哥他也得癌症死了。 “怪可惜家的,你是跟谁过?” “二叔。” “就是二领得,小时候孬得不能行。”刘长补了一句。 “怪可怜的孩子。”二香说着便扭头叫:“伊莲拿把糖来。”而后又对木根说:“你爹可是个好人哩。 不大会儿,从屋里走出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女孩子穿一身洁白的连衣裙,扎着一个高高的羊尾小辫,白嫩的小腿上套着雪白的袜子和米黄色的高跟凉鞋。木根不敢正视眼前这个女孩,他似乎在哪里见过,是在电影里,或许是在画书里,她就是城里忒洋气的那类。二香叫她什么“伊莲”,整个村里,木根所听到的、脑海存的就没有这样洋气的名字。女孩蹦跳着来到木根面前,长长的睫毛下面,双大眼睛充满着善意:“给你。”伊莲将一把糖递过来,木根不好意思接。 “接着吧,孩子,可怜的孩子。”二香说。 “接着吧,木根。 刘长也附和说,憨厚而皱巴的脸上仿佛都是笑窝。木根便红着脸,伸出双手去接伊莲递过的五颜六色的糖。二香眼直瞅木根的手,似乎看看他手上有没有怪指。伊莲递过糖后便转过身移步向屋里走去。木根捧着糖,呆愣愣地看着仙女似的伊莲在模糊中消失。 夜里,木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儿,脑海里总抹不去伊莲的影子,忽而是伊莲的笑容,忽而是伊莲的白纱一样的洁净,那一团白露一样的柔软,柔软中的绵甜。木根就想起童年时无边无际的花地,无边无际的绿地,和那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他在河边的草丛里,踩着一簇簇的野花,追赶着一只蜻蜓,追着追着就过来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穿一-身白色的裙子,在花丛里忽闪忽闪地出没,那不是伊莲吗?木根想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伊莲向他眨着眼笑着。等他走近时,伊莲转身向河边飘去,白雾一样地飘去,飘着飘着就在河面上飞逝了。花茫的河面上,雾蒙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木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失身了,童男第一次的丢失,遗落在那甜蜜的梦里。 这以后,村子里天天都是二香的故事。二香买了村里的三面环水的场地,二香在那块地上盖了一处院子,二看在临街的房子里开了个饴铬面馆。 有人问:“二香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有人就答:“还不是那卖干货的东北野男人给她留的。” 有人又问:“听说她外边头多着呢?” 有人又答:“钱再多也不是什么好货。 ...... 二香不管那么多咬舌话,天天将饴路面调制得香柔爽口。村人说是说,慢慢地就聚集到二香的面馆来了。二香就喊伊莲,伊莲便蝴蝶似的飘到这位跟前叫声叔您吃好,飘到那位跟前叫声伯您慢吃。这个发育较早的女孩,两个馒头似的乳房已经显得膨胀,屁股也已圆浑,加上她毫无遮掩的野笑,将面馆里所有的魂全给叨走了。 闲下时,二香养一群鸭子,将鸭子赶进水坑里。二香种一园子石榴树,石榴花鲜红得让过往的行人,都想餐食。伊莲就把石榴花插在头上,一蹦一跳地在坑边“哟哧、哟哧”地赶着鸭子。二香的生意越做越好,先是乡里的,后是县里的,甚至市里有客来到这地儿,也不忘驱车来吃一碗二香的饴铬面。不知二香真的是面做得好,还是一老一-少女人长得好,反正,村里出了不少议论,说二香哪是面馆那是鸡馆,你没有见那院子里还留客吗?那二香是啥人,野男人出车祸死了,她将赔的钱和人家的家财全部席卷而来,把人家正道的妻儿都苦了。 二香不管村人咋说依然如故地做着生意。刘长却在人们的纷纷议论中,不知不觉地病了,又不知不觉地去了。他的儿子刘杰守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尽管一切花销都是二香出了,儿子刘杰在掩埋了父亲后,好和二香一阵子撒野,将父亲一生的委屈全部倾吐出来,末了卷起铺盖卷,外出而走,一去而不复返。 丈夫的死、儿子的出走,没有影响饴铬面馆的生意,二香仍然谈笑风生,伊莲仍然“咯略”野笑。所不同的是伊莲大了,已经长成了二十岁的姑娘了,已经是一朵开展的花了,已经从坐城里人的摩托变成小卧车车接车送了。村人们目睹那貌似公主的伊莲,钻进穿着各式怪异服装男人的车里时,一个个不自觉都将街门关上。 伊莲不再殷切地在面馆里喊叔伯,村里的人们渐渐地远离面馆。面馆晚上只开一会儿门,但是每天都有来往的车辆。不知谁出奇地买了一只橡皮船,而且将船放在水坑里,伊莲每天就坐在船上,搭起遮阳伞,轻轻地与鸭群共游。 这哪里是人,这简直就是两只妖精,一只老妖精,一只小妖精。这村妖的说法传遍了全村,最后传到二香和伊莲的耳朵里。 你说那不是妖,那是啥,跟人跑了,将人克死,回到家,将家人气死;生一个不明不白的小妖,怎么就姓伊了,伊是谁的姓,野男人的,野男人的怎么又带到了村子里。这个窝囊死的刘长,当鬼也是个软蛋鬼,怎么就不厉色吓人呢? 二香想终究招谁惹谁了,二香想自己反正是老了,伊莲嫁了人就平和了。二香起初是想让伊莲嫁个城里的,没想到几年来,没一个和伊莲动真格的,他们都是想占伊莲的便宜,占过后就嫌伊莲贱气。二香就想在村里找一个正当人家算了。可正当人家又嫌弃她们骚气。三里五村,几个混混整天想打伊莲的主意,为伊莲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二香终于将伊莲叫到眼前:“不是娘狠心,我看我们的路子也不宽,这村里没有我们的路子了,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看是不行了,谁让你是二香的闺女呢。 那天晚上,二香忽然把二领得请到家里,四碟小菜一-壶白酒。二香把酒斟上,二领得喝一杯就浑身痒痒,他不敢正视面前的女人。二香年轻时也是格外漂亮,二领得每瞅上一眼,夜里就睡不着觉。如今的二香虽然年龄大了些,但风韵犹存,在二领得眼里依然灿烂。但是二领得虽说脾气邪,却是出了名的正派人物,他不会受到眼前的老狐狸干扰的。二领得这样想着就又将一杯酒落肚。二领得这才凭借晚上的灯光看对面的妇人。妇人仍着蘑菇状的烫卷头,皙白的面孔一点儿也不像乡下的婆娘。妇人面颊着淡妆,少加修饰的睫毛下,一双眼睛仍然明镜犀利,能穿透人似的。二香刚娶来时,二领得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知道刘长娶了个俊俏媳妇。二领得也和其他孩子们一块去了。二领得想刘长怎能娶这么漂亮的媳妇呢。心不平,就趁一天晚上,将只癞蛤蟆放进刘长夜查里。刘长夜里尿尿时,蛤蟆一声“呱”将他吓得病了一个月。二领得想起这事不自觉地笑笑。三杯酒落肚,妇人终于开了言,沙哑的嗓音令人苍寒和惧畏。 “木根多大了?” “二十五。” “定亲了吗?” “找了,没合适的,人家嫌俺孤、穷。”二领得说到这儿忽然浑身有点不对劲,“咋了,他大娘想给木根办件好事?” “有这个意思。”妇人也端起一杯酒。 “不知是哪村哪户,谁家的亲戚?” 妇人端起杯同二领得碰一杯:“本村本户咱家的亲威。 二领得觉得不对劲,“谁?” “咱妮儿,你说可以吗? “什么?”二领得只觉得头嗡一下子,手中的空杯,“啪嚓”落在水泥地面上碎了。 “不配吗?”妇人沙哑的声音令二领得喘不过气来。 “配配,当然配。”二领得急忙回答。 “那就这样定了。”女人又将自己的酒杯斟满递过去。 二领得接过酒杯,没有立即喝,他思索了一阵子,想想自己是不是醉了,就看看对面的女人到底是人是妖。他仿佛看见妇人鄙视他的笑,就不自觉地将头摇晃起来:“不合适,不合适。“ “咋了? “木根不配伊莲,俩差得太多了,村里人会笑话的。 “我们不嫌弃木根,木根这孩子实在,我回来第一天就相中他了。过我们的日子,不要怕别人嚷嚷,好戏还过不了三天呢。 “只是太亏了莲儿了。”二领得将话咽下。二香听了这话昂着的头忽然垂下来,心一酸,眼角潮湿起来。 二领得自己又斟了一杯喝了,“将莲儿嫁给木根,难道是你的真心?’ 妇人的泪扑簌扑簌地滴在了桌面上。 二领得索性端起酒壶一气喝掉,然后振振有词地说:“不情愿嫁过去,我们木根就是第二个刘长,我们可不当这垫背的。”说完将酒壶“啪”地摔在桌上,趔趔趄趄地走出二香家的大门。妇人浑身一颤,瘫在床上。 从二香家出来,二领得没有及时回家,而是直奔木根的破西屋。木根还死猪一样地睡着。二领得将屋门叫开,一屁股坐在床上,让木根坐在椅子上。二叔点起一根烟后说:“奶奶娘,有人想打咱的算盘欺负咱哩。 “谁?”木根揉了揉眼说。 “还能是谁,西坑边那村妖呗。” “她咋咱了? “咋咱了?她想让咱给她妮做垫底呢。” “垫什么底?”木根一脸疑惑。 “她说让你娶她那女儿狐狸精,让你学刘长,你说咱能丢起这个人吗?” 木根听着听着明白了,原来二叔是被二香邀去给自己提亲,提亲的竞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天仙般的伊莲。这怎么可能呢,自己压根都不敢想这事。自从那次梦遗以后,木根就不能不想那女孩了。木根没钱买铪馅面,就故意蹲在面馆的对面,瞅莲儿的影,听莲儿的笑。石榴花开的时候,他站在堤顶上窥视满院的石榴花和那些石榴花中飘来飘去的少女。更惬意的是莲儿躺在橡皮船里,木根就借个土坑、土埂趴着窥视船里懒洋洋的女人。木根就想,如果能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哪怕一时一刻也不枉活一世。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二香会将莲儿嫁给他这个一无所有的孤儿,便激动地问二叔:“你咋说?”二叔伸了个懒腰,“我给她回绝了,将来闹出笑话,我可丢不起那人。”二叔说完后就困了,困了后就又说:“睡吧,别瞎想了,二叔就是给你找个外路媳妇也不能让你打光棍,不然,怎对得起我那早死的哥嫂。 二叔晕晕昏昏地走了,木根才扬起的喜悦又被二叔几句话给淡漠了。木根想,二叔怎么不设身处地去想想呢?想到这里,木根又想起那梦迷的影子,不觉得一种酸甜之流涌来涌去。 木根没敢惊扰二叔,独自一个人梦游似的来到二香家,在二香家的大门口从夜黑一直等到天亮。二香开门了,发现呆站着的木根,就怔住了。 “见你二叔了?” “吭。” “你二叔撒泼,你还来千啥? “我....林根不知从何说起,眼泪竟扑簌扑簌地落下来。 二香见状,也不再难为他,就把木根带进屋子,递给毛巾,让他擦擦祖,半天他还在抽拉着。二香想,叫他哭一会儿吧。等他情绪平静了,二香忽然怔住了脸: “我们莲儿也算是个角儿,嫁给你木根,自有嫁给你的目的。但你必须答应几个条件,你同意咱再说,不同意,就算扯。 “同意,同意。”木根已经没有了思想。 “那就好。莲儿从小到大,没干过农活,针线活,只会玩泼,结了婚后,一切不要靠她;莲儿她跟我惯了,她要在这儿住得多,在你们家住得少,到时候,你不要干涉。你有你的活法,莲儿有莲儿的活法,不要认为她嫁给你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你不要干涉莲儿同外人的来往,就是男人,你也不要充满醋意,这一条最重要。到时候觉得忍不住了,再反悔,我可不依你。答应这三条,就成亲,受不了,就回去吧。 木根没想到女人真狠,难怪二叔不让我娶这村妖呢,这话她竟能说出口,自己也是人呢。然而,一想到伊莲,想起那团白雾,想起自己的誓言,真是,你木根凭啥能拥有这样如花似玉的女人呢?这时,伊莲从卧室里出来了,穿着一件豆青色睡衣,头发随意地蓬松着,迷人的意欲让人突增恍然。木根不时地在她身上瞥来瞥去。伊莲见客厅有人,又旋即回卧室了。 二香说:“考虑的咋样,不行就回去考虑几天。 木根已坚定信心,其实他等了半夜,已经将信心坚定了,忙回答道:“不用了,我同意。 “同意了就好,同意了就不用再反悔。你的家境我清楚,定婚结婚一切消费不用你拿。另外,再给你五千块钱,将屋子里外整整。 二香说完后,就喊女儿:“伊莲,将那准备好的五千块钱拿来。 看来二香非常自信,而且早已有了准备。不大会儿,伊莲拖着鞋出来,将一沓子票子递给木根:“拿住吧。”木根忽然想起几年前,她递糖的架势。木根呀木根,木根感到自己真的就成了木头了。 木根用二香给的钱,将屋里屋外的墙刷新一遍,又铺了地板,吊了顶,还去会上买了几件家具。收拾完毕,二香过来验收,没有批评也没有赞扬,然后,就领着木根、女儿一块到城里,让木根洗洗澡、理理发、刮刮脸,又到时装店给木根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部翻新。西装一穿,领带一打,对着镜子木根简直认不出自己了。伊莲也制了一套婚纱装,之后就去照了张结婚照。 中秋节,木根终于将伊莲迎娶到家里。那天晚上木根圆了多年的渴望。伊莲端坐在床上,木根卧缩在沙发里,红蜡烛摆动着柔弱的光,窗外秋虫听鸣叫,夜露不时地凝聚在一起,落在叶子上,时不时有啪嗒啪嗒的响声。伊莲想窗外肯定是叶子坠落,叶子在飘零。 两人对坐无语到后半夜,伊莲终于支不住了,她去解婚纱,后面的拉链怎么也拉不开,就拾头低声说:“你过来一下。”木根昏沉的头脑被这天堂般的声音忽然唤醒,脑子猛一激灵。伊莲开始解头上的花饰,木根眼直呆呆地盯着。伊莲就又说:“你来一下呀,给我拉开背上的拉锁。”她真的开始说话了,他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一整晚上他都注视着她,那白色的雾团飘逸着,在他脑海里闪来闪去。有时,他真的就看到她慢慢地张开双臂,从床上飘了起来,她是不是又要向河边飘去,然后,淡化为无影无踪。他真有些害怕就揉揉眼,伊莲仍在,他的莲儿,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坐在他咫尺的床上。伊莲的叫声仿佛将他从刚才的状态中唤醒,他又揉揉眼,从沙发上站起来。大概在沙发里卧久了,他猛一起有点头蒙眼花,镇定片刻才过来。他挪到她身边,女人浓郁的芳香扑鼻而来,她已不同于那个给他糖吃的女孩子了,他走近她有一种肉欲。使他体内热血沸腾,心里怦怦直跳。“快些。”他的莲儿对他的呆级有些不满了,他急忙从那白白的柔纱中间寻那拉链,颤抖的手在她的背上滑动着,把她弄得痒痒的。她急了,“这不是吗?乱摸啥。”原来拉链就在她纤细的手里。他抓住拉链向下拉,拉链有点死绊住了,他就又回了几下,然后拉开了。她白白的脊背顿时裸露在他的眼前,他趁机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她一颤站在了床上,然后迅速地将双臂退出白纱。婚纱倏地从上到下自然脱到了她脚底,一个美丽的玉体,呈现在他面前,将他多年的渴望拨弄到了极点。他真的有点不敢看了,怕蹦跳的心弹腾出来,不自觉地闭上眼睛,不知眼前是飘逸的虚无,还是梦迷中的实在。伊莲已经钻进了被窝,一床大红色绣着龙凤吉祥的七色彩缎将刚才的梦整个遮掩。他站在床边凝视一团黑发以下她那张动人的小脸,忽然起了个想法,想将她的肉体整个读一遍。这样想着就放下被子,从桌上拿过一个手电简,然后大胆地钻进被窝里。大概手电筒碰到了她的肌肤,她身体一缩平躺过去,“你干啥?”“没啥。”便执拗地钻进被窝里,打开了手电筒,从上到下地阅读。她被他的动作给弄笑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想看就看吧。”说着就揭开了被子。他趁机扑卧在她身上,实实在在地抱住她。他渴望的女人,她再也不会化雾飞跑了。他扬起头,发现自己的脸正贴在她的乳峰间,女人肌肤的香浓,让他渴望得浑身燥热,令他饮食,令他吸吮,可他又一时找不到吮口,最后终于揭开了女人的乳罩,一个豆粒大的桑甚成了他餐饮的驻点。 他尽情地释放着他的渴望,仿佛在一层裹着的雾团里荡来荡去。女人既不反对,也不附合。女人忽然想起了家里满院子的石榴花,想起她毫不怜情的采摘,想起她将石榴花任意地摆弄,然后,又一把一把地撒在坑水里,任一群鸭子在花瓣簇簇的水面上游来游去。女人想着想着眼角一酸,泪水滚了出来。女人想自己不明不白的出生,不明不白的漂流,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乡村,一年能转几处学校,转得连课本都动荡了。父母的生活是个谜,忽而亲热如胶似漆,忽而争吵反目成仇,他们还不断遭父亲以前的孩子们袭击。父亲就是在他们无休止的争吵中喝醉了酒遭车祸死的。伊莲忽然又想起了城里的那个大男孩。伊莲天姿聪颖,而且会跳新疆舞,她的一个达板城的姑娘,曾经将学校的晚会推到顶峰。没想到她回家的路上,一个大男孩用鲜花挡住了她的归路。 “伊莲姑娘,送给你一束玫瑰花。 “我不认识你,你干吗?” “我是初三的余歌,一个你的崇拜者。 那余歌比她足足高出一头,一身运动服。余歌说他爱踢足球,瘦削的身材满有精神,“你将来准备做什么?” “不知道。” “怎么能不知道,考大学呗,我的目标就是清华、北大。 她艰难地摇了播头,她明白自己的成绩。没想到自己的归宿竟然如此。她的泪水已经流满了双脸,红蜡烛在激烈的报荡中忽明忽暗,烛泪已经顾着蜡烛下的白瓷瓶流到桌面上。 三天以后伊莲就回到了她的石榴园里。大大的石榴已经成熟,伊莲就挑选几个大的,用兜子兜住。秋风清凉、爽身,她就又坐在那橡皮船里,松开桨,任船儿无目的地漂来漂去。她掰开一个大石榴,将石榴的粒攥到手中,然后又-粒一粒扔进嘴里。多了,将一口嚼过的石榴籽喷到水面上。一群鸭子戏来,又都渐渐地远去。 一切都像没发生似的,伊莲的出嫁,就像农村一场古会,热闹一阵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二香的饴铬面仍然红火,伊莲的笑声又起来了。 面馆又恢复了以往的繁荣,门前的小汽车渐渐地多了,只是客人仿佛是引来似的。二香不允许术根住在石榴园里,伊莲也不来木根的家住,渐渐木根又恢复了从前的生活。 街上的闲言又出来了,这次出来矛头好像对着木根,也同时捎带着二领得叔。木根性软,二领得知道,他不希望木根做第二个刘长,这也就是他不同意这门婚事的原因,无奈侄儿鬼迷心窍。 二领得开始在石榴园附近晃悠了。他看见小车中的男人一进面馆,二香娘儿俩的贱笑,心里仿佛被蚊蝇叮似的。那晚,二领得喝醉了酒,一同饮酒的都拿他侄儿的事取乐。二领得终于忍不住了,他半夜来到石榴园,大门紧闭,他又绕到一侧爬上院墙,月光下,他隐约发现石榴园里停放着一辆轿车,他的心咚地一下快要蹦出来了,一种莫大的耻辱让他羞得满脸热辣辣的。他跳进园中,蹑手蹑脚来到窗子前。窗帘紧闭,柔弱的光线将整个窗子映得像飘柔的亮镜,一阵狎猥之言和女人的浪气从屋内传出。他双耳已经嗡嗡直响,羞辱和愤怒使他想一脚踢开房门,然而他没有。他转到屋门前,月光下他瞅见了门的搭链和一把锁,一个念头浮了上来,他用颤抖的手抓住搭链和锁然后将罪恶锁进屋里。 二领得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石榴园的,他跄踉地来到木根家,把门叫开,然后对着木根就是一个耳光。这一耳光将他的多日积怨和一晚的怒气,全部发泄了出来。“窝囊废,软蛋,你的媳妇偷汉子,你还能睡着觉。 木根被二叔的一耳光打醒了,多日来,村人对着他投来的异样的目光,仿佛那村妖真的附了他的体,他几次都想找伊莲说说,可见了伊莲话又咽了回去。他想起了二香的话,想起了他的应诺。如今,二叔一耳光将他打醒,他真的成了第二个刘长。 二叔拽着木根挨家挨户地找他们的近门人,又挨家挨户叙述他捉奸的细节,然后汇集二三十个人,向石榴园奔去。房门已被锁上了,愤怒的人儿,便抱起一根木桩,几下便把门撞开,谩骂声,吵闹声,汇集在一起,仿佛不是为木根出气,也不是为二领得出气,而是将多年的积怨一下子倾泻出来似的,人们都为有这一对村妖而脸上无光。 屋里的女人已经知道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也感觉到事情的后果。伊莲已经穿好了衣裳,二香浑身开始发颤,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在寻找出逃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准备,便被愤怒的人群拥倒了。“扒了她的衣服。”不知谁喊了一句,有人便将二香的睡衣撕烂了一块子,灯光下,女人的做气全没了,浑身颤抖着,蜷缩在床上。 伊莲一身的纱妆,被人挤压在里屋的墙角里,她一头散发蓬松着,仿佛感到死期的来临。这时,有人开始撕扯她的衣服了,她觉得不是痛苦,而是男人趁机在她的身上乱摸。当她听到,要扒她们的衣服时,下意识地将衣装挽紧。几个年轻的男人,说着去撕她的衣服,她蹲在墙角里,用一头乱发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时,忽然一个人拨开人群本能地扑在她身上,嘴里不停地说:“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而后,身上便被一阵拳打脚踢。 “没用的东西。”二领得又一记明亮的耳光,结束了人群的愤怒。人们顿时停住了喧闹,二香被撕扯得几乎一丝不挂,她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身子,身上明显有伤痕。伊莲仿佛没有看到,她从惊吼中醒来,发现有个男人护着她。她惊讶,这男人竟是自己的丈夫木根。这个本该最痛恨她的人。现在反而为了她受尽屈辱。她更加感到无地自容,便又将头发甩过来遮掩着脸,屏住呼吸。那个男人竟然也被打得流着鼻血,跪在地上,乞求饶恕。 问题终于在二领得的操纵下及时解决,那男人拿出五千块钱才被放行。第二天一早,人们还没起床,伊莲就从城里要来救护车,医院。 村里的人仍在议论那晚发生的事,仿佛从议论的快感中解脱多年的积怨。木根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他头脑昏昏,怎么也理不清头绪,不清楚所发生的一切是谁的过错,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 岁月渐渐地洗去了闲言碎语,人们毕竟还要生存,别人的事仿佛就是生活佐料,人们文周而复始地劳作着自己的土地,这天二领得忽然有事找木根,“木根呀,你怪二叔吗?二叔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刘长。”木根翻了个身,将脸面向墙壁。二领得猜不透这闷葫芦的脾气,就又说:“木根呀,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咱木家的名声啊。儿几天都过去了,打是打,闹是闹,你也该去城里看看你媳妇和你丈母娘了,这是我打听到的地址。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吧,只要你媳妇改了,还能过一家子好人家。”木根仍然一声不吭,二领得有些不耐烦,拾脚踢了木根一下,“地址我放这儿了,去不去由你。” 二叔走后,木根从床上找出伊莲她们住院的地址。他忽然觉得自已早该去一次,便爬起来,准备好东西,趁半晌街上没人,悄悄地溜出村庄。田野里春天的芳香顿时扑鼻而来,这么多天的阴霾仿佛一下子褪去。他从远处回望村庄,一种解脱感油然而生。 木根走在这座城市的街上,城市焕然一新,仿佛才梳理过一样,街道宽了,路面平了,新颖的路灯装点在空中,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绿地和花坛。木根想,几年下来城市变化很大。木根第一次来这座城市是根据二叔提供的地址来的,没想到二指宽的纸条让他寻找了将近一天。城里人不好打听路,等他来医院时,又在住院部找了近一个小时,最后从档案中发现,病号早就转院了,转到哪儿,谁也不知道。 从此木根便和伊莲失去了联系,妻这个还没固定的概念,就这样悄然淡化了。石榴园的石榴花该开的仍然开,水坑里的鸭子仍然在水里漫游着,只是那喧闹的铪铬面馆早已失去了旧日的繁荣。一把锁在雨水里浸泡着已经生了锈了,人们不再议论二香了。村妖的故事,慢慢地变得陌生起来,只是有人时不时逮一只鸭子炖一锅香嫩嫩的鸭肉时,还偶尔提起她们。人们在月光下,边吃着鸭肉,边叙述二香娘儿俩的劣迹。后来捉鸭子的事,二领得恼了,在街上大骂一通,又喇叭广播。鸭子一下子有了主了。接下来便撬开石榴园的大门,用三马车将能用的东西都拉到木根家。雨天过后,就下坑一个一个地将鸭子捉住,赶趟集卖掉,又将钱扔给木根,石榴园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木根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种大棚西瓜。木根就开始整天钻进大棚里,头茬西瓜五一前下来,卖好了能卖一块多一斤。接着就是第二茬,第二茬瓜下来时,大田的瓜正旺,价钱上不去,第三茬西瓜是秋后下来,弄好了,行情也可以。 伊莲的面孔渐渐地在木根脑海中淡化,淡化得自己都已经想不出她真实的模样了。这一天,木根忽然遇上件怪事,邮信的老张找到他的瓜棚里,给他--张汇款单。他非常奇怪,自己长这么大,别说是汇款单,就是书信也没有收到过一封,就忙问是哪里寄来的。老张戴上花镜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摇摇头。钱的数额还不小一一五千元,木根只好将这事藏起来,钱一点也不敢花而是存上。隧后这种事每年都要发生一次,木根对这神秘的事虽然有疑惑,是不是 还有个莫名其妙同名的人呢?然而整个街上是没有的。可能是伊蓬,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了那早已淡化了的事,但怎么想理由也不充足。他趁月光明亮的夜晚,从瓜椰里出来,独自一个人回到村里,绕水坑转上一圈,幻化中鸭子戏着水,水面上浮着橡皮船,伊莲撑着遮阳伞在哟池哟池地赶着鸭子,然而鸭子没了,人没了,船也不知让谁给弄走了。他跳进院子,石檳园里荒凉一片,屋门上者锁,蒿草很高,残败的石榴树被草遮掩着,一个石榴也寻不到,一些调皮的孩子早已将石榴娃都采去了。木根这样夜游者仿佛多了个夜游的病,有时,睁开眼是场梦,有时也发现自己半身湿漉漉的。村上便有人说在夜间隐隐见到一个人出人石榴园,石榴园闹鬼的故事 也随之传开了。 这天夜里,他正在瓜棚里,忽然被汽车的鸣笛声惊醒,一个妙龄女郎,飘然而至,他使劲揉了把眼,看是梦不是。女郎走过来,一个熟悉的面孔顿时将他记忆唤醒,“伊莲。”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真的是伊莲,伊莲将他从瓜棚里接出来,然后坐上轿车向城里飞驰。伊莲又像结婚前似的,给他整头,理发,洗澡,订制衣服,然后又焕然一新地让他看看自己的模样,除黑点,还有点色彩。伊莲驱车来到郊野,在一个绿树环抱的地方,有一所学校。在学校里拐了半天,来到一栋教学楼前。伊莲便下车走进教室,不大会儿,从里边领出一个小女孩。伊莲将她抱到车上,女孩见到他,有点认生,伊莲便对木根说:“你的女儿,珠珠。”木根呆了,自己怎么会有女儿了,他打量这个叫珠珠的女孩,六七岁年纪,着一身白色连衣裙,活脱一个伊莲再世。然后他瞅着珠珠的轮廓真的有些像他了,还有那塌陷的鼻子,简直就是他们木家的翻版。这一点儿也不假。自己怎么就有了女儿呢。他记得伊莲和他在一块的时间很短,伊莲离开村的时候也没有一点儿显形。他正疑惑时,那个叫珠珠的女孩忽然叫了他一声爸爸,然后慢慢地向他偎过来,“爸爸,我也有爸爸了。”女孩说着说着泪水流了出来,“爸爸,你真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吗?你搞勘探工作,你是在寻找矿产,寻找宝藏吗?”木根不知道女孩嘴里在说什么,伊莲替木根哼着,珠珠便用小手抚摸着木根的脸,“你的脸被晒黑了,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木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上课铃声响了,伊莲将珠珠抱下来,珠珠依依不舍,木根顿时觉得眼眶湿润了。伊莲说:“妈妈早就去世了。”她原本是恨他们,后来,有了珠珠,有了她和他的结晶,伊莲便觉得木根就是她的根了,所以就给他寄钱。伊莲说她在外面飘荡得很辛苦,她辛苦的目的是让珠珠以后不再像她这样辛苦,她让珠珠从小就受良好的教育,让珠珠过着城市上等人家过的生活。她还要让珠珠上大学,甚至她想到让她出国深造,总之她要从珠珠的身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她又说,本来她不想再与那村庄有瓜葛了。可是珠珠长大了,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世,需要父亲。她几次想租个父亲算了,但是,她忽然不想再欺骗珠珠了,就把木根叫了过来,只是对珠珠仍然说,你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你爸是搞勘探的,是寻矿寻宝贝的,她不想让女儿知道她是农民的女儿。 女儿,木根自从见到了女儿,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多年的离散,父亲的形象陡然形成,珠珠是他和伊莲的结晶,这是不可置疑的,珠珠的美貌也是不可置疑的。他木根也可以有个仙女一样的女儿,女儿将在伊莲编织的童话中天真地活着,活出一个与木根世代都不一样的世界。也许伊莲走的就是这种捷径。他木根知道有个叫珠珠的女儿就可以了,她是他木根的骨血,她要在伊莲的塑造中成为城里的洋学生。伊莲还说什么?有条件能出国的就出国,这个世界他木根从没接触过,也没敢想过,他忽然自卑得不敢做珠珠的父亲了。 “你完全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儿,不必在瓜棚里折腾自己,我每年给你寄去的五千块钱悬够你零花的了。”伊莲拿过他粗糙的手有些微怨,有些负疚。伊莲租了个宾馆,让木根与她短栖了几天。有天夜晚,木根起来小解时发现伊莲眼眶里的泪。伊莲说在外边做事也太难,像她们做事的程度,都不好活上大寿;伊莲又说,飘零的生活总要有个根,你木根就是她和珠珠的根,你木根就是她珠珠惟一的亲人,你木根要将家侍奉好,把石榴园也侍率好。 石榴园要改观了,木根在伊莲的指点下,将石榴园建造了一套公寓,城里人设计的,城里人来施的工。公寓豪华气派精巧别致,公寓闲雅舒畅。公寓要花很多钱,村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连二领得这次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公寓临街的大门镶着“珠珠公寓”四个大字。 “珠珠公寓”的落成,像给村里建了一座梦幻楼阁似的。人们又说起了二香,谈起了伊莲,谈起了铪铬面馆。人们似乎弄不清刘长与木根的区别了。木根仍然种他的西瓜棚,只是隔三差五地打开“珠珠公寓”的大门,打扫一下院落,浇一下花草,他已听惯了各种声音,各种闲言碎语。他每进一次公寓,就仿佛看到了伊莲和珠珠飘忽的身影,快乐的嬉闹,,那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木根在城市的街道上毫无目的走着。要不是那赖皮的瘪三骗了他一车瓜,又当众寒碜了他,他绝对不会走进这座城市。他拿着瘪三给他的三张纸条,耳边忽然想起瘪三挑衅似的惨笑,“你老婆是鸡,你老婆是鸡,你老婆是发廊的鸡,是歌厅的鸡,是桑拿间的鸡。”随后瘪三就写下这三张纸条,递给木根。木根当场将纸条撕碎,愤怒地望着瘪三说不出话来。然而,当瘪三的背影消失后,他浑身颤抖,一片一片地拾起碎纸片。他终于在瓜棚里失眠了,也不愿再到珠珠公寓。他打着卖西瓜的幌子到城里寻妻去了。 往期作品回顾: 朝君 雨过荷塘 朝君 梦里走失的妹子 朝君 黑槐花开 朝君 白的雪花的狗 朝君 隔着车窗的雨 朝君 在诗经的岸边等雨朗诵:金笛 沐过你心田的春雨(外二首) 梨花雪(外一首) 朝君 王朝君 屋后的枝,房前的花 王朝君 莲心河 王朝君 与子书 王朝君 云朵,飘过枣乡 王朝君 搭起七夕思念的鹊桥 王朝君 盘坐乡音 蚊虫叮咬里,采撷你一脸的青涩 王朝君 王朝君 唐诗律魂——沈佺期 王朝君 枣林(外一首) 王朝君 家在河的上方(组诗) 作者简介王朝君,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水利文学协会副主席,内黄县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集《门泊桃红》,小说集《我想像中的父辈们》、《寨外》。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莽原》、《奔流》、《大众诗歌》、《中国水利报》等。电视散文《有水的地方》获年度河南省电视文艺牡丹二等奖;散文诗《放风筝》获全国首届会龙杯散文诗大奖赛佳作奖。 支持原创,赞赏作者 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nxuebaomam.com/slhcs/885.html
- 上一篇文章: 王选低处的光阴
- 下一篇文章: 一份比较齐全的潮汕土话quot对照